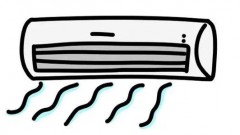(资料图片)韩少功做客华中科技大学作题为“文学在电子时代的变与不变”的讲座。
韩少功
有些东西到了可以总结的时刻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隗延章
本文首发于总第884期《中国新闻周刊》
麓山脚下,作家韩少功和11位老同学拍了一张合影。他开玩笑地借“竹林七贤”的典故,给这张照片取名“麓山十二贤”。这是发生于1981年湖南师范大学的一幕。他们都是该校77级的大学生。
毕业临别那天,“十二贤”在韩少功家聚会,兴之所至,他们相约5年之后,同月同日在他家再度聚会。
五年之后的那一天,韩少功早已忘记此事,正因工作忙得焦头烂额,突然听见有人敲门。他打开门,见到从外地赶来长沙赴约的同学杨晓萍。“十二贤”中,只剩下杨晓萍一人还记得当年的那个约定。站在屋内的韩少功感到吃惊和惭愧。
多年之后,2008年3月,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217教室,该校77级中文系3班的50多位毕业生集聚于此,22年前错过的约定,终于在这一天被弥补。
韩少功将这段经历,写入了最新的长篇小说《修改过程》。与他以往故事发生在乡村的那些作品不同,这本新作的故事发生在都市,正巧讲述了一群77级大学生30年间的命运变化。
修改过程
其实,早在20年前,韩少功便尝试写作77级的故事。那次,他写了8万多字,觉得不行,废掉了。之后他一直惦记,但总是觉得时机不成熟,“不熟悉、没感觉、拿不准、没必要,都不能写”。如今,韩少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去年年末,海口一座临江的楼里,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追逐金钱的马湘南,追逐权力的楼开富,追逐自由的肖鹏和陆一尘,追逐尊严和情怀的史纤和林欣纷纷在韩少功头脑中鲜活、清晰起来。他觉得时机终于成熟,正式开始写作《修改过程》。
写作中,一些人物在他头脑中继续生长,渐渐变得和他最初的构想不同。比如商人马湘南,构想中,他只是一个追求利益的人。写作中,一些细节不断从韩少功头脑中冒出来,最终马湘南变为一个“两面人”,即便是政治也可以被他做成生意。
文中的中文系教授肖鹏,一边写作,一边怀疑文学的意义。最初,韩少功在写作这一内容时,是以肖鹏自言自语的方式呈现的。初稿写完之后,他引入了思想家惠子,让惠子与肖鹏在小说中对话,探讨文学,他们的一个话题是:文学能多大程度地呈现真实?
如今,韩少功的写作生涯已经超过40个年头,他和小说中的肖鹏一样,对小说能多大程度呈现、影响真实,越来越感到怀疑。于是,他这本小说采用戏中戏结构。让自己笔下的一个人物在书中写着另一本小说,两条线索彼此影响和互相改变。
对于小说中一些人物命运的结局,韩少功呈现拿捏不定的态度,干脆交给读者去选择。他为来自乡村的史纤在同一章设计了AB两个结局。从文本层面而言,韩少功的这一次创作显得很“实验”。
“把小说写作过程撕开,一方面有意削弱小说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倒也可能强调一种自我揭秘的坦诚态度,在另一层意义上赢得读者更大的信任,加强了某种‘真实感’。”韩少功说。

1981年,大学期间,韩少功(后排右一)与其他同学所组成的“麓山十二贤”合影。
乡贤
虚构的《修改过程》中,网络小说写作者是中文系主任肖鹏,他记忆力消退之后,决定辞去系主任职务,将自己关在一个套间中写小说。真实世界里,韩少功从未在中文系做过系主任,也没有将自己关进套间埋头写作,在写作者的身份之外,他有着更广阔的生活。如今,他每年有一半时间生活在海南,一半时间生活在汨罗八景乡。
早在30多年前,韩少功便有下乡生活的想法。他和妻子梁预立是在他知青生涯中相识的。1985年,妻子在他的《诱惑》一书的跋中说,“我们悄悄约定一件事,请允许我暂时不说,我们期盼那一天早日到来。”后来,梁预立说,她提到的那件事,便是去乡下生活。只是,真的实现它,又过了很多年。那年年中,韩少功活跃在文坛,以“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被充分认可。
1998年,韩少功的女儿读大学,不再需要他和妻子操心。城市的生活,也让他越来越觉得疲倦,那时他在海南任作协主席、文联副主席、《天涯》杂志社社长等多个职务,“会议、应酬、还有审读,要占掉我一大半的时间。”韩少功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他们夫妻二人决定实现搁置多年的心愿。两人先去海南的乡下考察,但因为不懂方言,与农民沟通不便,最终放弃了。他们又走遍老家长沙周边200公里的村庄,还去了湘西等地,兜兜转转,最终选择在汨罗八景乡,一个有山有水的库区。
韩少功以2000元一亩的价格,买下一片凸进水库湖区的荒地,委托给施工队盖房。他告诉施工队,盖成与农民同样的样式,砖墙、瓦顶、木头门窗。房子建成之后,他去八景乡,却发现农民的房子都是铝合金门窗,墙上贴着瓷砖,他自己的房子反而显得“土”。
2000年,韩少功辞去《天涯》杂志社社长的职务,与办好内退手续的妻子以及一只叫做三毛的长毛狗,一起迁入汨罗市八景乡。
在这里,韩少功生活中的有些方面,比农民还要农民。屋里的家具,是用梓木打的,连树皮都没有刨去。他种地不用化肥和农药,而是去学校公共厕所的粪池挑粪施肥。蔬菜长虫了,他戴上老花镜,用手捉虫子。
但他并未隔绝与外界的交流。他有一辆捷达车,可以随时进城。他的住所安装有宽带、传真机,可以远程处理工作。只不过,有时工作会被在城里不会遇到的意外打断:一次打雷,他家的五件电器全部烧坏。
韩少功并没有把自己去往乡下的生活做出文学化甚至诗意化的解读,他觉得自己的选择就是求清净。
乡下住久了,韩少功渐渐融入当地的生活。农闲的日子,他会在八景乡四处转,有时走进一户人家聊上一个上午或下午,然后抓起筷子,吃完饭再走人。农民逢喜事设宴,喜欢请他。乡村才子写古体诗词,也会找他斟酌。
他也逐渐介入当地的公共事务:他给村干部讲课,教他们讲正气、守规矩和与村民沟通的技巧;在儿童节去附近的小学,给孩子们讲怎么写作文;附近学校交学费那天,让妻子守在收费处,资助交不起学费的孩子;利用自己的资源,给周围的村庄牵线搭桥,引入政府和社会资金建桥、修路。
和韩少功一起成名于1980年代的一些作家,有的也像他一样选择了去往乡下,先锋作家中的洪峰、马原就是例子,只不过,他们对当地生活的介入,没有韩少功多,与村民的关系,也没有这样亲近。
韩少功从城市刚回到乡村时,村民也是议论纷纷,很不理解。如今,村民早已将韩少功当作自己人,叫他“韩爹”。甚至一位村民还为他考虑起后事,要给他选一块墓地,地点在山坡还是平地,都为他考虑周详。这让他哭笑不得。
即便去往乡村之初,韩少功也没有任何生活以外的目的,但一点点融入其中,渐渐有了记录的想法,在汨罗八景乡住到第七年,他写下长篇随笔《山南水北》,把在这里的一切生活经验都纳入其中。

1988年,移居海南的韩少功。
不止于寻根
很多人见到韩少功如今生活在汨罗市八景乡,以为他出生于乡村。事实上,韩少功出生在长沙市,直到在1968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才第一次去往乡村生活。
他插队的地方在汨罗天井茶场,距离如今生活的八景乡只有20公里。那时,他的生活,远没有现在自在,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回到茅舍,连抽7支烟都缓不过来,坐下来能立即睡着。
那时,他与村民的相处也并非都愉快。他办农民夜校,给村民讲巴黎公社,劝说村民斗走资派,村民却只对识字和治鸡瘟有兴趣,在他贴出一张抨击茶场领导多吃多占的大字报之后,被村民举报,遭到隔离审查。
但这6年的知青生活经验,成为韩少功日后写作中最重要的精神资源。无论是他在“文革”后期创作作品,还是他在1977年进入大学之后,发表于《人民文学》早期代表作《月兰》,几乎都是乡村题材。
1980年代,韩少功积极回应着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色彩,参与了很多活动,但他也渐渐看到那些热情运动中的人性暗面,他渐渐感到某种程度的幻灭,开始从那些实际的行为中抽身回到文学,1985年,韩少功提出了“寻根”的概念。彼时,一系列文学运动渐次展开,文学圈进入了最热闹的时刻,先锋派、现代派、新写实主义几乎同时登场,而相较于那些学习西方技法的同辈作家,韩少功更像是大踏步地“撤退”,但这种撤退有着更深的文学自觉,他所说的寻根,并非只是退回传统,而是一边扎进中国传统,比如楚文化,另一边扎进异域文化,将它们彼此碰撞、融合,重新阐释传统。
这一年,他想起在知青期间见到的一位只会说“爸爸爸”和“×妈妈”两句话的小孩,以及“文革”中的湖南道县惨案,创作了日后声名大噪的《爸爸爸》。理论家刘再复高度评价说,“《爸爸爸》延续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主人公)丙崽的思维病态,是一种文化上原始愚昧。”
在文学世界中向“根”跋涉的同时,韩少功也开始学英语。他陆续翻译了毛姆、卡佛等人的作品。不久,他又与二姐韩刚,合译了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有一个情节:托马斯与特蕾莎驱车到一个熟悉的小镇,但是,小镇的街道、旅馆、疗养院等公共场所的名称,在苏联入侵捷克之后,几乎全部俄国化。两人面对物质上熟悉的小镇,却感到巨大的陌生感,以至于无法在小镇过夜。
这本书里的“误解小词曲”一章似乎也启发了韩少功。从这之后,他找到了编织故事情节以外更多的方法,比如以方言、俚语为突破口,试图揭示语言表层下深藏的集体无意识和长期积淀的民族心理结构。多年之后,他创作的《马桥词典》《暗示》,便是这种影响的产物。
近几年,他开始回忆自己知青、大学所处的时代,写下《日夜书》和近日出版的《修改过程》。这两本书,讲述的都是一群人在中国飞速发展的这些年命运的变化。
他对这种命运的变化的理解,与他写作之外的现实经验分不开。1981年大学毕业之后,他除了写作和回到汨罗生活,还曾在一些地方政府挂职,在海南办杂志,在作协、文联任要职,这些经历,让他切身体会中国数十年间的飞速变迁,有机会观察时代变迁中的人们。
韩少功60岁之前的写作,从未像近年这样,连续用长篇小说的体量,审视、解剖自己早年所经历的时代。他曾这样解释,“有些东西你30年前是看不清的,人生要落幕的时候,整个历史要完结的时候,有些东西到了可以总结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