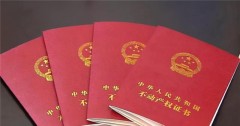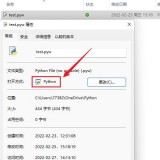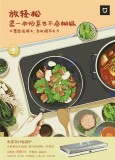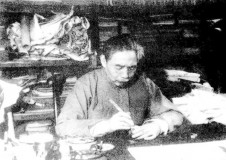黎巴嫩真主党政治纲领的调整及其实践
孙寅兵
(长治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系,山西 长治 046000)
摘 要: 1989年黎巴嫩内战结束后,真主党审时度势在政治纲领上做出了调整,即由激进的伊斯兰教思想调整为务实的政治主张;相应地,在实践层面,真主党积极参加议会选举、继续从事抵抗以色列的军事斗争、开展广泛的社会福利活动,最终实现了自身由激进民兵武装到合法政党的转变。
关键词: 真主党;黎巴嫩;政治纲领

1982年,黎巴嫩真主党在伊朗与叙利亚的支持下秘密组建起来,以从事针对以色列及西方国家的恐怖暴力活动为外界所熟知。1989年,《塔伊夫条约》的签署宣告持续了十五年之久的黎巴嫩内战的结束。之后,真主党以军事武装与合法政党的双重面目示人,逐步坐大的真主党与2006年挑起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冲突。因此,探究1989年前后,真主党在政治纲领上的调整及其实践活动对于理解认识未来黎巴嫩政局中的真主党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一、真主党政治纲领的调整
大致以1989年为界,在此之前,真主党在政治纲领上以激进的伊斯兰教什叶派宗教思想为主,致力于尽快在黎巴嫩建立伊斯兰神权统治秩序;在此之后,则以较为宽容的政治思想为主,积极推进真主党的黎巴嫩化。真主党政治纲领的调整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教法学家监护”的问题
1982年至1989年期间,真主党在该问题上的观念是,主张在黎巴嫩立即建立由伊斯兰教教法学家监护的伊斯兰共和国。1982年创建之时,真主党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承认十二伊玛目的宗教权威及其不谬性,伊玛目能够正确理解《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教法。同时,真主党承认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为先知与十二伊玛目合法继承人的领袖地位,拥护霍梅尼“法基赫的监护”(教法学家的监护)的主张,即伊斯兰教教法学家的神权统治。真主党创始人之一的赛义德·穆萨维,曾就教法学家与建立伊斯兰国家的问题作过一番深入的分析。他认为,穆斯林应该顺从真主安拉及先知,推翻不公正的统治者,以建立一个平等公正的,同时在穆斯林之间消除混乱与歧视的伊斯兰政府,即应尽快在黎巴嫩建立一个霍梅尼式的由伊斯兰教教法学家监护的伊斯兰共和国。
1989年黎巴嫩内战结束以后,真主党在实现教法学家监护、建立伊斯兰神权统治的问题上发生了转变。具体如下,由于真主党笃信教法学家监护的思想,同时又将霍梅尼尊为穆斯林的伊斯兰教法学家,因此,在宗教上极大地依赖于霍梅尼的真主党将涉及黎巴嫩国内的一切事务都交由霍梅尼裁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如此,霍梅尼还是给予真主党一定的自决权,允许真主党根据黎巴嫩国内实际情况对“圣裁”加以灵活运用。198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后,伊朗对真主党支持有所减弱。真主党尽管仍然坚持教法学家监护的思想,但无奈不得不在黎巴嫩国内事务,尤其是黎巴嫩内战结束后的战略发展问题上表现出更大的独立自主性。而这种独立性与自主性,从战后真主党对黎巴嫩局势的分析与自身在黎巴嫩利益的判断上可以看出。
在关于建立伊斯兰神权国家的问题上,真主党将其作为该党的政治理想,而在政治实践层面采取了更为务实的政策。真主党不再呼吁建立教法学家监护下的伊斯兰神权国家的迫切性,转而关注黎巴嫩国内的政治现状,抨击黎巴嫩的现行的教派分权制;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批评基督教马龙派垄断政治权力这一范围,而是呼吁改革黎巴嫩现行政治体制、按照比例代表的原则改革现行选举制度等等。因此,在政治纲领中,真主党作出的调整为,由狭隘地坚持建立由教法学家监护的伊斯兰神权国家向过渡到推行黎巴嫩化的政策[1]。
(二)关于推行黎巴嫩化的问题
黎巴嫩化,主要指1989年黎巴嫩内战结束后真主党积极参与黎巴嫩国内事务的活动[2]196-203。1982年初创之时,真主党对黎巴嫩国内事务的总体观点是尽快建立教法学家监护的伊斯兰神权共和国,因此对于黎巴嫩国内事务多持消极的态度,如敌视基督教马龙派的统治,声称黎巴嫩(内战的)厄运的罪魁祸首是基督教马龙派;认为自身肩负着解放黎巴嫩国家、打破基督教马龙派对政治大权垄断、解除教派分权制政治体制束缚的使命[3]200-203。
但是,随着198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伊玛目霍梅尼的逝世、伊朗外交政策的转向以及真主党领导人在战略上的抉择,真主党逐步开始积极参与黎巴嫩国内的政治事务,从而开启了其黎巴嫩化的进程。对待黎巴嫩国内占据优势地位的基督教教派,真主党一改之前批评、不合作的态度,主张在公开、透明的氛围中积极与基督教派展开对话与合作,强调在不威及其他教派利益的前提下谋求达成共识。但是,真主党推行黎巴嫩化,积极参与战后黎巴嫩国内政治事务,并不意味着它对黎巴嫩现行政治制度的认同,相反,真主党在其政治纲领中依旧强烈批评黎巴嫩的政治制度,称其腐败至极,不可救药。真主党提出并力推黎巴嫩化,更多的是基于参与黎巴嫩政治生活所带来实际利益的政治考量。真主党遵循伊斯兰教教法、将《古兰经》中协商、多元等思想加以灵活运用,使其参与内战后黎巴嫩政治进程的决策合法化。因此,黎巴嫩化集中体现了内战后真主党关于自身发展战略的思考。
(三)关于吉哈德的思想
吉哈德是阿拉伯语Jihad的音译,源于《古兰经》中“为真主之道而奋斗”,意为“努力、奋斗”,即通常所说的“圣战”。吉哈德分为大吉哈德与小吉哈德。大吉哈德,指与个人的私欲作斗争;而小吉哈德有三层意思,分别指用生命与敌人作武装斗争的吉哈德、捐助财产支持真主之道的吉哈德及宣扬伊斯兰真理的吉哈德。
1982-1989年间,真主党对吉哈德思想的强调主要集中于战场上的对敌斗争。黎巴嫩内战期间,真主党活跃于黎巴嫩南部地区及贝卡谷地。此时期强调吉哈德思想,意在鼓励其成员积极从事抵抗以色列的军事斗争,同时也包括与个人私欲作斗争的思想。强调在进行军事斗争以前磨练个人品格、勇于牺牲自己生命的重要性,注重对成员进行系统而严格的训练,战胜私欲,培养成员内在强烈的自我牺牲意识。
1989年黎巴嫩内战结束后,真主党将吉哈德的意义逐步由战场上的对敌斗争转变为参与国内事务及参加议会选举上来。小吉哈德,即真主党在南黎和贝卡地区从事抗以斗争,在这个阶段仍是真主党主要的活动。但在这个阶段,真主党进一步丰富了大吉哈德的内容及加大了大吉哈德运动的比重。大吉德除了包括与个人私欲作斗争的意思之外,还指积极致力于黎巴嫩政治体制的改革、参加市政地方议会选举及参与政府行政工作,也指在实践上与黎巴嫩政府的腐败行为作斗争[1]。因此,此阶段真主党大吉哈德运动意味着更加密切地融入黎巴嫩的政治体系,同时致力于被解放地区和其他被压迫地区的经济恢复与重建工作。
(四)关于对待西方国家的态度
1982-1989年期间,真主党对待西方国家的态度主要表现为激进的反以抗美思想。1985年2月,真主党对外发表《致黎巴嫩和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公开信》。在这封公开信中,真主党将美国及以色列当作主要的敌人,认为黎巴嫩穆斯林所遭受到的伤害都是美国及其代理人以色列所带来的,因此真主党将摧毁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作为其奋斗的目标之一。真主党反以抗美的态度是如此坚决,以至于丝毫没有与以色列谈判的余地。另外,真主党激进的反以抗美思想实际上是其反抗西方文明的集中体现,历史上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尖锐对抗以及近现代以来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的殖民统治是真主党根深蒂固敌视西方的原因。真主党敌视西方国家,也体现在其对法国等国家发动恐怖袭击的实践上。
1989年以后,真主党对待西方国家的态度有所调整,将斗争的矛头主要对准美国与以色列。真主党将“大撒旦”美国与“小撒旦”以色列作为压迫者,并呼吁所有的被压迫者奋起反抗。在对待其他西方国家的态度上,真主党的仇恨则相对弱一些,对法国、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都采取了开明的政策。对待国际组织,真主党则采取了合作的态度,比如重申遵守国际人权宪章以及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加强与当地及国际福利与发展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合作等。
二、黎巴嫩内战结束后真主党实践重心的转移
1989年10月,黎巴嫩议会通过了“实现民族和解”的《塔伊夫协议》。《塔伊夫协议》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战后黎巴嫩教派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叙利亚在黎巴嫩的驻军等问题。按照《塔伊夫协议》的规定,黎巴嫩议会议员的席位由原来的99席增至108席,并在基督教与穆斯林之间平均分配;叙利亚驻军在两年内协助黎巴嫩正规军恢复主权,在黎巴嫩选出总统、建立和解政府、实现政治改革的任务完成后即从贝鲁特及其周围地区撤至贝卡谷地,然后再同黎巴嫩新政府谈判全部撤军问题。随着1989年黎巴嫩内战的正式结束以及《塔伊夫协议》的逐步履行,真主党在思想上实现由激进的伊斯兰什叶派宗教思想向较为务实、宽容的政治思想的转变,相应地在实践上真主党通过积极参与国内政治事务,实现了由激进民兵组织到合法政党的转变。
(一)参加议会选举
1989年黎巴嫩内战结束后,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精神领袖穆罕默德·侯赛因·法德拉拉曾指出,在教派分权制下的黎巴嫩通过革命实现向伊斯兰统治的过渡及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此,通过逐步改革的方式来实现前述目标是非常必要的。故而通过参加议会选举的方式,进而融入黎巴嫩政治体制中去就非常必要。伴随着政治纲领的调整,真主党在内战结束后做出的最大调整便是积极参加国家议会的选举。表1中列出了真主党在内战结束后的历届国家议会选举中所获得的席位情况。
1992年,黎巴嫩举行了内战结束后的首次议会选举,真主党获取了27个什叶派议席中的8个席位;1996年议会选举中,真主党不断宣传其在南黎的抗以运动,打出“他们用生命在抵抗,用你们的投票在抵抗”这样的口号,进而赢得了9个议会席位;2000年,真主党携以色列最终撤出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胜利成果,再获2个议会席位,达到了11席。而在1998年与2004年的地方市政议会的选举中,真主党同样取得巨大的胜利,掌握了贝鲁特南部郊区和黎巴嫩山省所有的什叶派市政议会[4]127-129。
表1 1992-2005年黎巴嫩国家议会选举27个什叶派议席归属情况
因此,真主党在内战结束后参与国家议会选举的成果是非常显著的,逐年增加的议会席位,也使得真主党成为议会中不容忽视的一支什叶派政治力量。真主党参加黎巴嫩国家议会的选举并不代表着它对黎巴嫩政治体制的认同,相反,真主党在议会中多以普通民众的代表身份自居,扮演着反对派的角色,拒绝加入黎巴嫩政府,并多次在各种场合对黎巴嫩现行的世俗教派分权制进行批评。
(二)继续抗以大业
黎巴嫩内战结束后,真主党实施调整的另一个表现是其军事武装力量得以保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从事抵抗以色列的军事斗争。根据1989年《塔伊夫协议》的规定,黎巴嫩境内所有民兵组织必须予以解散,关闭其军事训练基地,同时上交武器。[1]150-102这对视军事武装力量为生命的真主党来说是真正的考验。前述已谈到,真主党在战后积极参加议会选举,为其扩大了政治影响力。但真主党武装力量的保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叙利亚的支持。黎巴嫩内战结束后,叙利亚在黎巴嫩国内占有特殊的地位。自1976年叙利亚军进驻黎巴嫩以来,已控制了约占黎巴嫩全国3/4的地区[5]40-42。1989年《塔伊夫协议》中对叙利亚何时全面撤军的问题并未给出明确的规定,只是含糊地提到叙利亚驻军在黎巴嫩选出新总统、建立和解政府的两年后即从贝鲁特及其周围地区撤至贝卡谷地,然后再同黎巴嫩新政府谈判全部撤军问题。由于在内战结束后黎巴嫩国内的特殊地位,加之牵制以色列的战略考虑,叙利亚在真主党军事武装力量的问题上采取支持的态度。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积极的抗以活动,最终迫使以色列于2000年选择从黎巴嫩南部全部撤军[6]278-282。
(三)开展社会福利活动
黎巴嫩内战结束后,真主党社会福利活动的范围也逐步扩大,从内战期的对参加抵抗活动的民兵及家属提供抚恤金及其他帮助扩展到建设惠及黎巴嫩什叶派的基础设施工程。真主党所开展的一系列社会福利活动,主要包括筹办建筑公司,开办学校、医院、药店及小额贷款公司等[7]99-110。这些设施一般设置在什叶派的地区,但其服务人群面向所有需要帮助的人;真主党的医院与诊所对前来就诊的病人,不论其政治派别或宗教派别,通常只收取少量的费用。真主党将大量的资金用于社会与医疗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资金大多来自伊朗的援助,金额通常在每年1亿美元左右。此外,真主党积极投身于黎巴嫩的战后重建工作,组建了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圣战重建基金会”,并在战后重建的任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真主党社会福利活动的开展,为其赢得了更多黎巴嫩人的支持。
三、真主党政治纲领调整及实践重心转变的原因
以上分析可知,1989年黎巴嫩内战结束后,真主党在实践层面上向积极参加议会选举、继续抗以活动以及广泛开展社会福利活动的转变缘于其在政治纲领上的调整,即在政治纲领上实现了由激进的伊斯兰教思想到务实的政治主张的转变。真主党之所以能够实现如此转变,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真主党是叙利亚、伊朗实现地区利益的重要工具,其政治纲领的调整与实践的转变得到了来自叙利亚与伊朗的大力支持。对叙利亚来说,保留真主党的军事力量是制衡美国、乃至对付以色列的棋子。实现黎巴嫩民族和解的《塔伊夫协议》中,叙利亚在战后黎巴嫩政局中享有特殊地位,即对黎巴嫩政治重建的粗暴干涉。叙利亚居中调解,实现黎巴嫩当局与真主党的和解。真主党调整政策,对黎巴嫩当局采取接受态度;黎巴嫩当局则承认真主党激进民兵武装为反抗以色列的民族力量。对伊朗而言,支持真主党有利于实现坐大的地区利益,同时也能有效地分散来自美国的压力。从真主党的创建,到发展壮大、再到政策调整及实践的转向,无不与伊朗的支持密切相关。
其次,黎巴嫩什叶派的政治诉求——强烈要求参与战后黎巴嫩政治生活——迫使真主党作出调整。教派分权体制下,黎巴嫩什叶派的权益长期以来被当局所忽视。但经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什叶派政治觉醒运动后,该派参与政治的意识愈加强烈。代表黎巴嫩什叶派利益的真主党不得不考虑什叶派民众的要求,在政策及实践过程中作出相应调整。
最后,真主党审时度势的结果。黎巴嫩内战结束后,依据《塔伊夫协议》的规定,黎巴嫩当局宣布“黎巴嫩境内所有民兵武装予以解除”。这对依靠枪杆子成长与壮大起来的真主党而言,无疑是严峻的考验。在伊朗、叙利亚的支持下,真主党认识到参加议会选举是其走向合法性的必由之路。因此,真主党审时度势对其政治纲领进行了调整,在实践上也转变到参与战后政治生活中来。
参考文献:
[1]Joseph Elie Alagha.The shifts in Hizbullah's ideology: religious ideology,political ideology and political program[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06.
[2]Eitan Azani.Hezbollah: The Story of the Party of God: From Revolution to Institutionalization[M].Palgrave Macmil-lan.2009.
[3]Sami G Hajjar.Hizballah:Terrorism,National Liberation,or Menace[M].DIANE Publishing,2006.
[4]李福泉.从边缘到中心:黎巴嫩什叶派政治发展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07.
[5]Judith P.Harik.Hezbollah: the changing face of terrorism[M].B.Tauris,2004.
[6]彭树智.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M].王新刚,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3.
[7]Augustus Richard Norton.Hezbollah:A Short History[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The Adjustment of the Hezbollah’s Political Platforms and Its Practice
SUN Yin-b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Tourism Management,Changzhi University,Changzhi Shanxi 046000,China)
Abstract :After Lebanon’s civil war was ended in 1989,Hezbollah has made the adjustment of the political platform,which changed from the radical Islamic ideology to the pragmatic political proposition.Accordingly,in the practice,Hezbollah took an active part in parliamentary elections,the military struggles against Israel and the extensive social welfare activities. Finally,Hezbollah has achieved the shift from the radical militias to the legal political party.
Key words:Hezbollah;Lebanon;political platform
收稿日期:2017-01-25
作者简介:孙寅兵(1986-),男,山西襄垣人,助教,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