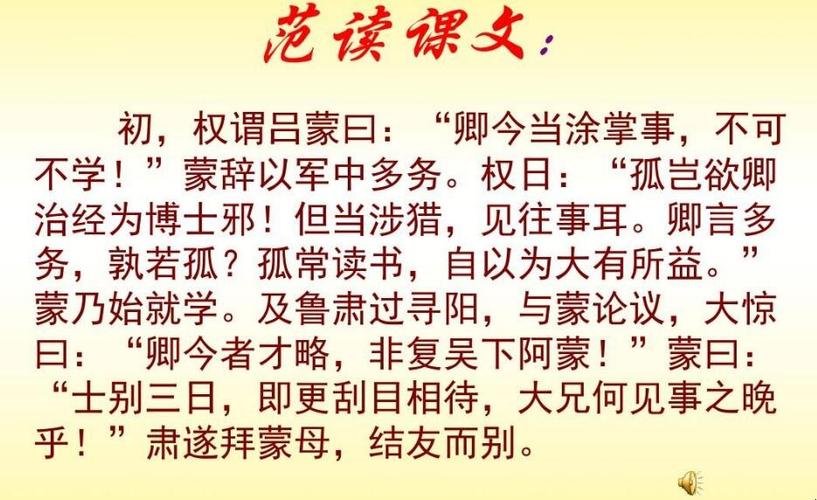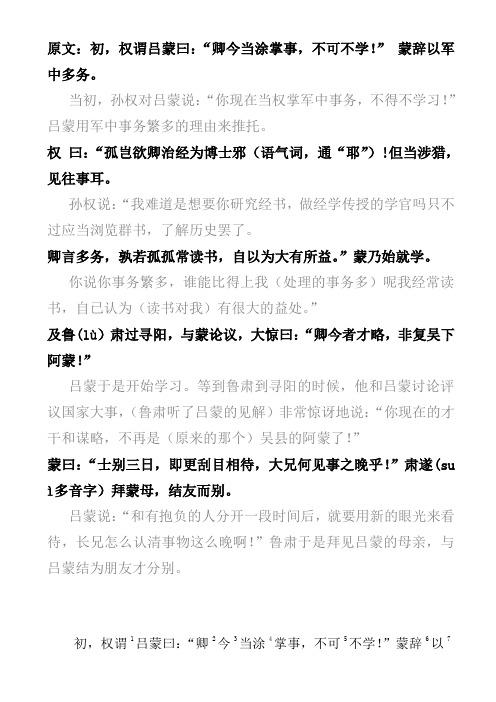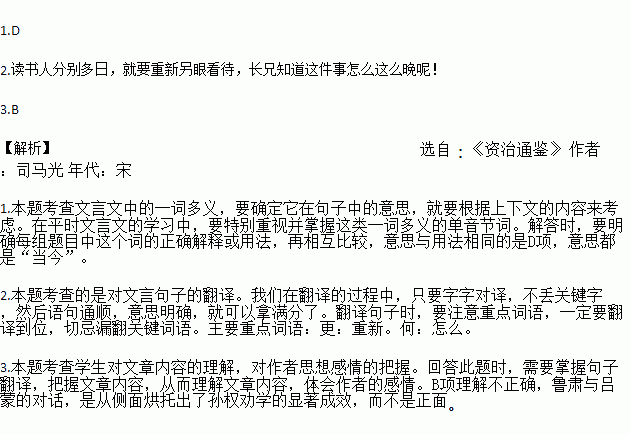青春是一段淋漓尽致的旧时光文/布月童/////每个人都有三种面孔我不喜欢跟周围的人变成完全一样的。身边这群人像聒噪的鸟群,千篇一律,爱凑热闹,爱做白日梦,爱追随年级最出风头的人物,爱讨论肤浅的电视剧和偶像派明星。惟一的青春期过后,他们将再无可骄傲。我向往电影或小说里那些别致的女孩,她们总是单独地穿梭在城市里,眼角眉梢挑起来,狡黠的目光比湖水还要粼粼动人,像只消失在晨雾中的白毛狐狸,让追捕不到它的猎人怅惘兴叹。她们常常让成年人还深感恐惧,占据了青春,还占据了智慧。语文课本上苏东坡写“遗世独立”,我特意用红笔勾出来。在学校,没有几个人准确地记得住我的名字,因我并不常常像班长一样愚蠢地站在讲台上哗众取宠;也没有几个人听说过我的心事,因为我觉得把敏感的情怀讲给太多人听是种矫情的事。有次停电,大家点起蜡烛玩不留名游戏,发言人收到的其中一张纸条是留给我的,他念:“周生生。你是一个傲慢、神秘、不一般的女生。你能不能剖析一下你自己?”所有人望向我,那时,我正蹙着眉嗅班上某位女生的气味,我不是欣赏她的香水,我只是热中于玩猜前味、中味和后味的游戏。好多双眼睛一下子期待地看着我,可是,我只是说:“每个人都有三种面孔,一个是自己眼中的自己,一个是他人眼中的自己,还有一个是,真正的自己。你要听哪一个呢?”我凛凛地扫过每一个人,果然没有一个人敢接住我的目光,敢回答我的话。既然是不留名游戏,当然是胆小鬼才敢在这时候不负责地发问。我笑了笑,又继续猜着白麝香和紫罗兰到底有没有在香气里面。灯光重新亮起来,大家都把蜡烛当生日蜡烛一样许愿后再吹息,我也一样,我希望我自己,把最好最年轻的年华,不庸碌不媚俗地过完整。然后,我吹灭它,带着一层笑容。/////为什么必须是我?期中考的成绩发榜了,我不意外自己又是年级前五十名以内,我不想像书呆子一样天天熬夜看书辜负风景,也不想像无知少女天天幻想少年和未来,我认真上课做笔记,考试前抓紧复习一下,这样稳定的优良成绩理所应当。路过教导室,我被班主任叫住,他先是赞扬我稳定发挥,又挥了挥手,招过站在墙角像松柏一般挺立存在的俊秀人物。我记得他。林迦南。 他是前两天才被全校通报批评的人物。早会上被罚在全年级面前念悔过书,他吞吞吐吐念到一半,突然不耐烦地吼:“张新群。后面这个字怎么念?写得这么潦草我怎么看!”学生们哗然大笑。张新群被班主任揪着耳朵揪出来,求饶:“是他逼我写这一千字的悔过书的!我不写他就会揍我的。”那时候他在台上,眼眸如没有云层遮挡的星光,闪耀着逼人的灼亮。周围人气急败坏,他反而笑起来,嘴唇卷着彩虹一般弯弯的弧度,他不怕天塌下来,不怕地陷下去。那副什么都不怕的模样,竟然让他成了学生心目中的英雄。青春事太少,所以要自己生事。好像每个学生都藏着动乱的心事,只是有些人胆小地压下去,就像穿着统一校服一样毫无性格,而有些人却火山爆发。但是他会关我什么事呢?我疑惑地看老师,他局促不安地抿了抿嘴唇,似乎还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他把林迦南推到我面前,说:“同学之间互帮互助,以后你利用课余时间辅导林迦南的同学学习好吗?”让这样一颗定时炸弹跟着我?这种事平常不是落在班长或学习委员的头上吗?我才刚要摇头,老师却果断地说:“周生生。必须是你!”必须是我?我惊讶地看着老师,那种复杂的神色我猜不透,而林迦南太过靠近的气息更令我心烦意乱。我抱着书本,满腹狐疑地离去。/////我的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我不是一个听话的人,听话的人太像提线木偶,优柔寡断,毫无主见。林迦南当然更不是一个听话的人,否则为什么没有一天他不惹事生非?老师吩咐下来的事,我们俩都听过便忘。他翘课,上课趁老师板书的时候从后门溜出去,就在我面前,甚至近得我能闻到他头发里的青草香。但是我没理他。只是下课的时候,班长敲敲我桌子说:“周生生,老师让你进办公室。”我一向不进去打小报告,也不进去论功讨赏,更不进去低头认错,我几乎从不涉足这个官方场所。我满腹疑惑地去了,然后像被一道闪电给劈焦了。因为老师跟我说:“周生生,林迦南的学习是你负责的。他现在逃学了,你去把他找回来!”只要他打架的对象不是我,只要他考试作弊没有牵连我,只要他惹事生非没有连累我,我本来完全可以把他当作一场青春叛逆剧场来观赏,看后记得评论一句幼稚。我郁闷地走出校门,路过商店时看到一对亲吻鱼,你把它们拉开,但是它们还是会被一根线“噗噗”拽着亲到一起。我和林迦南竟然也有一条这么线,他走我也得走,只不过我们是撞到一起!我在桌球室找到林迦南。他潇洒地一球入袋,然后扔掉杆,陪我走出来。从烟雾缭绕的室内到空气清新的室外,我心情稍微好了那么一点。“你喜欢我?”他带着窃喜的神色。本来老师说得那番话已令我像个荷包蛋一样外焦里嫩,现在他这一句话更让我连心都焦得冒烟了!他以为我是那些单蠢女生,迷恋他敢于反抗的男子气概,着迷他精于耍坏的叛逆风姿,我竟然不惜跟他一起翘课,追他到天涯海角。“当然不是!”我大声地否认,“老师逼我的!”林迦南想起上次的协议,露出被吓一跳的样子。我们都没想到老师居然履行得这么彻底。回到学校后,老师吩咐爬墙逃校的他写英文悔过书,吩咐我一同留校纠正他的语法错误。太阳便渐渐地西斜了,最后落下去,换了一片月光与星光。林迦南的英文实在有够烂,连什么时候用be动词都不清楚。我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画画消磨时间,努力克制自己的怒气,不允许自己轻易受影响。大概是我频频看表让他看出端倪,他咬着笔杆子问我还有事吗?我不情愿地回答:“小提琴课,所以你快点搞定。”林迦南走过来,坐在我的桌子上,从高处看我。“你会小提琴?”他又抢了我的本子,看了几眼吹声口哨,“你画画也很好!为什么大家从来都不知道这些?”我平静地看着他,一句话也不说。而他让他大拇指的银戒指在空中漂浮和移动起来,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收回他的戒指,眨眨眼,说:“以物易物。告诉我原因,我就把悬浮魔术的秘诀告诉你。”我受不了诱惑,只能回答:“像个猴子一样对众人迫不及待的耍宝献艺有什么好呢?总让我觉得像孔雀开屏,有种谄媚的态度在里面。”我喜欢自娱自乐,当别人的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时,我的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这是一种藏在心底的骄傲,就算别人看不见,却可以支撑着你挺直背穿行过人群,如同锦衣夜行。而林迦南,他的戒指再浮起来,眼角眉梢也都一起愉快地浮起一个笑容。这有什么好开心的?/////若为自由故班主任教的科目是数学,这次数学小测,看着他坐在讲台上怡然自得的模样,我真的很想很想故意答错题,故意考糟了,然后以林迦南拖累我学习的理由和他重归生疏。但是,我又深深吸口气,痛恨自己的孩子气和不成熟。对于这种不合心意的小事我何必在意呢,生活中常有人令我怒,令我忧,令我的节奏乱糟糟。很小的时候我跟爷爷学茶道,耐心地等待茶叶醒过来,芬芳四溢,只为了修炼宠辱不惊的心态。于是,该怎样答还怎样答,得一个真实的分数。但是我在试卷的右上角用大一号的字写:“老师,如果我让林迦南门门功课都及格,你就要免掉我对他的责任。”试卷发下来,我有一个高分,以及一个“OK”。我回头望了林迦南一眼,恰好,他的目光也等着我,他竟是常常这样莫名其妙地看我么?先把这些放一边,当务之急是怎样把我们两个解脱出来。放学后,我跟林迦南说只要他考一次门门及格,我不用再辅导他,他也不用再被我管。我打个响指,容颜罩上一层光,像看见了重归正轨的以后,我说:“若为自由故,你暂且收起你的肆意妄为吧!”林迦南看了我许久许久,那种表情我再熟悉不过,像我受伤的小弟弟,关了灯躲在床下,我伸手去捞他,他身子反而越往里缩,黑亮亮的眼睛有种蝶翼轻拍的脆弱。不管怎样他说了好。我把我精心准备的笔记递给他,声音忍不住欢快起来:“熬几次夜吧,以后你就不用管我了。”“你也不用管我了是吗?”他收好资料,轻轻地笑着,却听不出阳光或彩虹,反而似下雨的小巷。而后,他离开,我愣了半晌,也离开。这样一个林迦南,莽撞冒失而荒唐,挥霍了青春之后一贫如洗,实在没资格侵占我太多思想。值得我在意的是什么呢?我的未来,我的生活,还有我的李明夏。李明夏已经是个大学生了,我记得他是因为在512大地震的时候,大地晃荡不安,我们像一群受惊的雏鸡一样,唧唧喳喳又浑身颤抖。可那时候全校都在自习,老师都在开例行教职工大会。高一级的李明夏最先一个人反应过来,他指挥所有人先钻到桌子底下,然后等震况稍微平静的时候,让所有人到宽旷的操场上集合。大家都慌不择路,他却一直很镇定地沿班组织,直到老师前来。他到我的班级时,我的班级乱成一团,他一瞬间看到冷静的我,说:“把你们全班人马上组织到操场好吗?”时间匆忙得不容我点头,他就已经相信了我。事后,我在荒芜的景色里找到面色苍白却眼神坚毅的他,那些平时敢斗狠的坏学生在此刻都还颤栗不安,独有他巍峨如青山。“周生生。我叫周生生。你呢?”后来,常常听见人谈起他,大家充满了惊叹,平日里毫不起眼的他竟然在危难时候最有担当。大家翻出缄默的他从不谈起的荣耀,攀岩冠军或野外生存挑战赛资格。他听到,不否认不吹嘘,一笑而过。已和他熟悉的我坐在他的单车后座上,怀有一种骄傲的心情。9月之后,李明夏去上本城的大学,只在高中留下传奇。我依然少有社交活动而欢喜看书。我听信亦舒在书中写的:“真正有气质的淑女,从不炫耀她所拥有的一切,她从不告诉人她读什么书,去过什么地方,有多少件衣裳,买过什么珠宝,因为她没有自卑感。”我渴望《傲慢与偏见》里的场景,伊丽莎白不惧地位悬殊,与达西先生在光影交错里优雅地翩翩起舞。/////你喜欢锦衣夜行虽然李明夏的生活轨迹已与我不再重合,可我常常去他的学校找他,他依然光芒内敛,认识他的人都说他给他们一种很可靠的感觉。他的生日,我破例走到餐厅的舞台上,借了演奏手的小提琴,低低说:“献给李明夏。”然后流畅地拉奏起来。他高兴地接受了我的礼物,问我最近高中生活怎么样。我皱着眉,只回忆起一个林迦南。不知道他有没有认真背书,虽然他的确有勤快地找我问学习上的问题,可是每次和他单独留校辅导很久,我总觉得他并没有专心在书本上,反而时不时想像个熟人一样和我开玩笑。接下来的一次月考,果然证明我的顾虑。他不仅没有及格,而且有一道题明明前一天我才特意教过他,他居然一样错得离谱。我忍耐了许久的怒气还是发作了。而看着我的愤怒,他踢倒了桌椅,在夜色里如呼啸寒风,冷冰冰地问我:“你喜欢锦衣夜行,那为什么又要在餐厅里为一个人拉小提琴呢?”为什么?而他又有什么资格问我这个“为什么”吗?我沉默地走出去,却遇见老师,他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又拍了拍我的肩膀,像某种信任,某种责任,某种期待,某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即是说,我和林迦南再怎么不情愿,还是得被绑在一起。于是,我和林迦南依然貌合神离,我给他补习,补习时他什么都懂,而考试时他什么都不懂。他找一百种借口来敷衍我的不满,而每一次,他的忧伤都比从前要漫上来一点。学校里的人都走光了,我和林迦南今天还在继续死磕。有人敲窗,我抬头一看,是李明夏,他要带我跟着他的社团一起到海边露营,看流星雨。我说很快,只剩一道题了。而那一道题,已看得出思路清晰的林迦南突然又混乱起来,求到了一个不可能的数值。一个小时过去了,他古怪而固执地要我讲解一次又一次。“明夏,你和他们约的时间快到了。那你先走吧。我可能去不了了。”我带着微笑送走李明夏,然后失去从容地回过头。“你故意的!故意不会做,故意不及格!你都是有意要捉弄我是不是?”我终于想了林迦南的臭名昭著,他擅长叛逆,擅长的是走到与所有人的期望相背的一个极端,他以为这样挑战别人的底线就是在昭示自己的力量。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眼睛里没有得意,却泛起雾气般的朦胧,然后声音穿过云雾,抵达这寂静的星球。“没错。我都是故意的。我故意不会做。我故意不及格。”很好!我亮出手机,刚刚我按了录音键,这时候耍点小聪明拯救自己,是我无可奈何。听到这段录音的老师,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再勉强我。事情平息以后,我长长地吐一口气,终于觉得这世界像新鲜剥壳的荔枝,柔润甜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