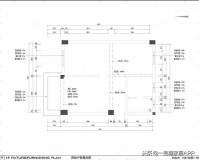胡赳赳

《论家用电器》,汪民安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版
作为一个理论专家,汪民安化身为一个长舌妇,喋喋不休而又絮絮叨叨地发表他对家用电器的长篇大论。这是一件很过瘾的事,原因很简单:之前没有人这么做过。
如其说这是对家用电器的“陌生化审视”,毋宁说这是作者写就的“产品说明书”,当然,这是一份供哲学家和学者消遣的产品说明书。它表达的是与这个世界的妥协和凝思——几乎每个句子,都是在向卡夫卡的一段话致敬,卡式的这段话是这样说的:“你完全没有走出屋子的必要。”显然,我只是引用了这段话的第一句。某时,我有和作者一样的心境。作者的书斋一般并非我们想像中的,是由独立的、豪华的、洁净如样板间的书房构成,在这里不被打扰、有咖啡和茶、明亮的灯光,能胜任阅读与写作。恰恰相反,作者的书斋往往要混杂着生活气息,妇女儿童的萦绕,并且被不断涌来的琐事打断。想起这一点,作者不免会对那些高大上的书房生起艳羡之情,然后回过头来一看,当一切退为背景之时——总有那消停的片刻——一切又是那么可以接受:家庭内部空无一人,只有作者的幽思;从沙发到书桌来回换位阅读,更换姿势时也更换一些不同趣味的书籍;忽然脑海里有了某些片段句子,正在神往之际,不免洋洋得意一番,还未等扑向“电脑”,就已经退潮而忘却了;“冰箱”间歇式地嗡嗡作响,它会有辐射吗,它会不会对智者的脑力有所损伤,下次千万不能把“手机”放在床头;如果过于寂静,是否该弄出一些声音作为背景音呢,昔日的“收音机”已经被蓝牙音箱兼容了,调到国际广播电台音乐调频,或者是喜马拉雅广播,收音机,这昔日的荣光,其功能还在,然而尸骨却无存。
环顾四周,唯有一种陪伴是长情的,这长情的陪伴,来自于物而非人,来自于普普通通的家用电器,其中一些完全不具有陪伴感:比如“洗衣机”,它偏于一隅,它沉默而低调,只在旋转时发出声嘶力竭的喘息。但是作者把自己的意识投射、贯注于其中时,“物自体”便获得了生机,获得了关照。也可以说,它获得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拟人化”操作,它在作者这里,意外地获得了生命。仿佛作者吹了一口仙气,它便复活了。它拥有了自己的“意识”,它所拥有的意识来自于作者浇灌的意识,然后作者用自我的意识与物的意识进行对话。
因此,卡夫卡说,你完全没有走出屋子的必要。在屋子里,每天都会发生不为人知的重大变化。只要你沉潜于此,既便不沉潜于此亦无可能,因为反正你也不怎么出门。这些变化意味着:熵的高低;秩序的更叠;物品摆放位质的变化;书籍的折痕;光线是无比重要的,它和人的情绪关系莫大;在坐着不动健脑和起身活动健身之间纠结。
大多数作者的关照是将生命体作为永恒的歌颂物:一朵花、一只猫或者斜刺里逃窜的蟑螂。汪民安勇于打破这种程式,他扩大了标的物,他从有机体推到无机体,他认为无生命之物也是值得歌颂的,并且有歌颂的绝大理由。歌颂的前提是拥有激情,激情推动着写作欲望。而对于汪民安这样的深思者而言,歌颂必须是理性的,诗意不容泛滥。歌颂也必须是遵循某种理想原则的,这个原则有着学理化的背景,但又必须偏离其正常轨道,不至于沦为枯燥干瘪之物。
因此他在写作中,特别注意不要过多引用、甚至就是基本不引用他人的论著。一切能不能由主体性自我完成?一切能不能像一个人写给一个冰箱的情书?一切能不能通过书面语言的“转译”生成对普通物品的美学转换?
这或许是一个小小的挑战,汪民安挑战式的挑衅了一下,试试知识界的接受度。国内的反响反而不那么容易获知,因为它既不学术,也不通俗。它难以归类。其语言当然是清晰的、明辨的,具有本雅明式的优雅。这是一部杰作,昭示着汪民安的玩童之心。
意外的回响反而是在国外。不仅在2018年翻译到了英国,而且大约有两篇文章评论到了这部书。其中一篇是由加拿大的安德鲁-彭达基斯所写的,题目是《灯之絮语:汪民安论现代电器的隐秘知识》。这位作者显然着意于其理论框架,称其表现的是与“能源人文科学”“新物质主义”的背景有关。他将汪民安的写作归结于“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以及“哲学上的左派”。作者隐隐对汪民安的叙事表示赞许,并且提示其与“风格与思想密不可分”的本雅明有同构的关系。而这正是“文学、美学和美文所具有的反思世界或者改变世界的能力”。作者将其看作是“理论与美学相辅相成”。
译者谢少波是一位跨文化理论的研究者,他将《论家用电器》翻译成了英文著作,其书名则有所变化《Domestic spaces in post-mao china:on electronic household appliances》,也就是《后毛泽东时代的家庭空间:论家用电器》。这儿有一个小小的吸引关注的策略,就是使用了“后毛泽东时代”。事实上,不如称之为“中国现代性的家庭空间”更为准确,毫无疑问,这些家用电器都是现代生活的范本,都是现代性缓慢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也是中产在追求现代观念的道路上所具有的“物的观念”。在这个观念的冲击下,我们才可以理解从波德利亚的“消费主义”的来临,到巴塔耶的“耗费主义”的丧失。
安德鲁-彭达基斯部分地理解了汪民安的知识谱系,比如他说:“汪民安的写作,在理论上受惠于福柯、本雅明、尼采和马克思,但是,在风格上,或许更接近于巴特,正如巴特那样,汪民安迷恋日常物品的无意识层面。”但是必须指出一点,知识谱系、秘密写作和肉身经验往往是密不可分的建构,我们很难指认一位作家其风格或思想的建立,是机械式的或是复刻式的,是受诱导还是受启发。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而言,这种“风格与思想、理论与美学”的发酵如同酿造师的独特眼光、经验、配方,以及增加一点点运气。仅仅对于知识谱系来讲,汪民安有另外一条隐秘的线索,即他在年轻时代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这构成了他的精神底色,因此每每可以有诗意的泛起。几乎在这本书的每一篇文论的结尾,他都会落实到一个具体的场景,一种迁客的幽思,一种内心的独白。他理性的控制又使其不过于泛滥,使得“风格”仍掌控在优雅、不急不缓的、自如地节奏当中。
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更在于其自身所具的“肉身经验”,这也是由汪民安作为一个“迥异的个体”所带来的令人震撼的经验,在对物的迷恋和反思当中,他充当了家用电器的辩护人,并且同时担任了正方、反方的使命,而他是否就此也充当了审判者的角色呢?既便是,他的姿态也是宽容的,而非批判的;是温和的,而非激进的。因此,对于他“哲学上的左派”这个称谓,无疑是扣了一顶莫须有的大帽子。如果说,“左”和“右”对应着不同的立场:激进/保守;变革/不变;公平/自由……细分起来有无穷无尽的伎俩——那么,汪民安是试图超越或调和这种争论的,因为这种标签式的辨识度,原本就是个幼稚的游戏:它忽略了事物的复杂性和随机性。正如我们的行走规范:有些道路规驯了左侧驾驶,有些立法则规驯为右侧;然而当我们去公园或郊区漫步时,则是一种自由散漫的作风。激进可以解释为“对规驯的抵抗”,然而“抵抗规驯”又会成为一种新的预设,一种新的规驯:抵抗者在抵抗这条路线上得到了规范、训矫和奖惩。这或许便是一种现代性的悖论:笼子飞向一只鸟(卡夫卡原文为:一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
不管怎么说,安德鲁看到了汪民安《论家用电器》与波德里亚的《物体系》之间的延展性:汪的这个对具体场景的申论可以看作是对物体系的一种回应。波德里亚在《物体系》中说:“在多数的方式之下,物品是唯一可以真正合拍共存的存在者(existant),因为它们之间的差异,不会使它们像有生命的存有一样彼此抗衡,而会温驯一致地朝向我集中,而且可以在意识中毫无困难地相加。”波德里亚不仅发明了“物体系”与人的欲望之间的关系,也敏锐的指出,是物,而不是人自身,确立了人和世界的关系:“所有的物品都可以被占有、为心理能量所投注,或者是在收藏游戏中的情形中,被整理、分类、配置。如此,物品正是严格意义下的一面镜子:它所反射的形象只可以连续出现,而不会相互抵触。这是一面完美的镜子,因为它不反射真实的形象,而反射出人所欲望的形象。”(《物体系》,2001,上海人民出版社,104页)
但是毕竟二者所要阐述的立场是不同的,波德里亚是持有的一贯的“消费”与“物”的特征,他希图以此来解释社会形态所发生的关键性改变。而汪民安则更加地温情脉脉,他似乎是想要表明,人自体与物自体之间,是存在亲密关系的。不仅是人性上的、欲望上的、生理上的亲密关系,它也是人和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区隔于他人的媒介。汪民安的这种探讨更加深邃,也更加隐秘。他回到了那种秘密写作式的兴奋。这种兴奋回应着卡夫卡式的寓言,在此必须将卡夫卡的这句话予以录完:“你没有走出屋子的必要,你就坐在你的桌旁倾听吧。甚至倾听也不必,仅仅等待着就行。甚至等待也不必,保持完全的安静和孤独好了。这世界将会在你面前蜕去外壳,它不会别的,它将飘飘然地在你面前扭动。”(《误入世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但是我颇不喜欢另外一位评述者的口气,也就是汪书的英文著作的序言作者,英国的学者迈克尔-达顿为该书写序时,似乎在申诉这样一个逻辑:这本讲《论家用电器》的书,放在“后殖民政治”的丛书中的合理性。当然,这便也解决了一个小小的疑惑:书名为什么要加一个前缀,“后毛时代”。只不过,迈克尔-达顿的优越感激起了我个人作为阅读者的不适,他言:“在非西方的‘地域’内来从事理论研究——正是这一点让《论家用电器》具有‘后殖民’的基础。”当然,我的不适也就点到为止,毕竟这是他人对他人著作的评述,尽管其“收留”的含义余音缭绕。但是在其他方面,迈克尔-达顿显然为这位并不熟悉的中国学者下了一番功夫,至少召集了一次讨论,并且引述了这次讨论的诸多观点。严格来讲,这次讨论是有效的,并且触及看问题的不同侧面:比如将汪书与明代小品文尤其是《长物志》的并置分析,虽然未作深入而令人信服的论证,但至少提供了一个启发点,这实在是可以留待后者作大的发挥。还有,他至少为将汪民安的坐标置身于西方文化理论的某个序列而大伤脑筋过,并且在后现代理论、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之间盘桓。这也是“知识生产”的某种“缠绕”:汪民安阐释了家用电器,学者则要进一步阐释汪民安的阐释,对阐释权的争夺和占位构成了新的跨文化、跨文本的知识景观,也制造了无数的歧路和迷障。因此,我对汪民安对“知识生产”的研究也一向抱有某种警惕,除非他拿出新的项目,比如“反智主义是一种反知识过度化生产的主义”之类的纲领。如果是这个角度,我宁可称自己为一个反智主义者。
责任编辑:黄晓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