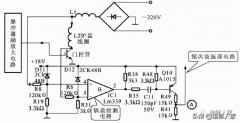作者:冷夕 来源:美篇App
十月,渐入深秋,天高云淡,清风送爽。不知怎么了,前些天连着数日,小时候与柴火的一些往事总是浮现眼前并进入梦乡,细一思量,发觉也许是因了储存在大脑里的年代记忆信息在释放,拨动着那些关于儿时深深浅浅的记忆。
自古以来,被人们俗称为“开门七件事”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以柴为首,可见柴火曾是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是人们生活的根基,是让人们得以果腹和取暖的有力保障。柴火,给人们带来了光和热,带来了温暖,也成了岁月长河里不会忘却的一份独特的记忆。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在大瑶山这个边远的山区,不只是农村,机关单位、厂矿企业、街上居民,全都是依赖烧柴生活的,除了单位食堂是买柴烧的,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是自家上山讨柴火的。
若时光回流到五十多年以前我们的小时候,这个时节正是家家户户进入积极储备柴火过冬春的时候,因为冬天天寒地冻,春天雨水多,不易讨柴火。于是就开始周而复始的干一件整个秋季最忙的活儿,去山里讨柴火。

这仿佛是一个全家齐上阵的活儿,天气刚刚开始转凉,不分男女老少都会燕子衔泥似的,肩挑人扛,从几里地外的山里一点一点往家里添增柴火。山间,巷口,院里,房前,经常看到一家几口砍柴火、背柴火、劈柴火、垛柴火的忙碌景象。在人们眼里,谁家要是柴火少,还会遭到别人的鄙视和笑话。用大人们对小孩子的话讲,不要像你们的课文里的《寒号鸟》那样,等天冷了,天天念叨:“哆嗦嗦,哆嗦嗦,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垒窝!”
不等进冬,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的柴火垛就开始逐日递增了,手勤的人总会把柴火码放得整整齐齐,既省地方烧取的时候又方便。堆放的柴火就像排兵布阵的士兵一样,在呼啸的寒风中不屈不挠地挺立着,给人一种肃穆又温暖的感觉。

一九六一年的秋天,父母亲从被下放到罗香乡的农村转回到了县森工局(林业局)工作,单位这时已改设在距县城四公里多的老山,一并建立了伐木场。老山,是大瑶山一个著名的地方,单单看名字,就会想到是一个充满着原始神秘色彩,林木参天、小溪潺潺、鸟语花香的地方。这座“神山”,成为了一代老山仔(妹)成长的地方,在那贫穷落后缺衣少食的年代,“老山”倒是平添了不少儿时的趣事,柴火,便是其中之一。
我那时刚六岁,但已经历了最困难的二年大饥荒的农村生活磨难,采摘过野菜,放养过小鸭群。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拾柴,成为了我每天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起先,只是在小河边搜寻捡拾涨大水时从山里冲到岸边的大水柴。一天,发现身边多了一个同龄人,在帮着捡拾柴火。俩人很快就熟悉了,才知道他是局长的儿子,叫梁学,从山外的七建农村的家里跟随父亲来了,他们吃食堂,所以用不着拾柴回家,我们成了好朋友。
在深秋的一个午后,梁学提议进山里面去拾柴,我和梁学背上竹筐,沿着屋后的一条小路,愉快地进了山林。山上的林木苍翠,高低错落有致,风光秀丽迷人。跟在梁学身后,我不时抬头仰望身旁的参天大树,苍劲挺拔,一眼望去,直冲云霄。梁学胆子比我大,一路埋头捡拾柴火,全然不顾身旁缠人的荆棘,而我却是有点小心翼翼的。初次进山,我们不敢走得太远,我一边捡拾地上的枯枝干柴,一边不时望向不远的屋子。

没多久,竹筐装满了粗细的柴枝,梁学喊上我,开始愉快的返程。忽然,一只毛茸茸的小松鼠挡在我们眼前,调皮的眼神里透着一丝不舍,仅停留了一小会儿,倏地一下钻进树丛不见了。
从那以后,只要天不下雨,我和梁学都会上山拾柴火。慢慢的,与大山格外的亲近起来。
在家里,兄妹中我是老大,除了拾柴,担水、扫地、烧火这类家务活也都落在了我的身上。那时侯,家庭的柴火灶都是用几块石头和土垒砌起来的,或者是就架个铁三角猫,一般是两膛灶,一膛煮饭炒菜用,用鼎锅煮熟饭后换上铁锅炒菜,一膛烧水用,固定放口大锑锅或大铁锅。灶前有个土陶瓮,有好的火炭时把火炭夹进去闷熄,或者是直接用水淋熄,攒储冬天烤火笼用。那时都没有条件砌烟囱,火烟直冲屋顶。每当晨曦暮晚,屋顶上飘荡的徐徐轻烟回旋上升,随风而逝,给山场增添了许多祥和的气氛,也饱含着家的温馨和温暖。

每到做饭,母亲把柴火放进灶膛点燃,我就得坐在灶膛负责看火续柴。这也是个“技术”活,急不得慢不得,要把火候拿捏得恰到好处,才能保证火力不大不小刚好着,添急了多了会压住火苗沤出一团团的浓烟,呛的人满脸鼻涕眼泪,添慢了少了火会灭,火太猛了饭菜会糊,火太小了又会做不熟饭。刚开始时缺乏专注力和判断力的我,坐在灶火前,总是不由自主地盯着灶膛里红红的火苗走神儿,不是添的太急弄的满屋烟,就是痴痴呆呆的忘了添柴让火着完熄灭。母亲耐心地教我:“人要实心,火要空心”。当灶里面的柴火架空了,火就呼啦啦地烧起来了。
柴火在乌黑的灶膛里熊熊燃烧,映着天真无邪的脸庞。小小的身躯坐在灶膛口的小板凳上,弯着腰,往灶膛里添柴。有时火烧得没有明火的时候,就用吹火筒吹吹,火旺柴烧成炭时,就用火钳夹出里面的火炭放进土陶瓮里闷熄。

人坐在灶前烧火需要技巧,并且要随时掌握火候的大小。柴火的干湿度、一次放多少,如何放?都在考验你是否用心和耐心。有一次,母亲叫我煮粥,我放了满满一灶柴,放任着整灶膛的柴火呼呼地燃烧。我拿着一本小人书,全神贯注地看了起来,全然忘记了锅里正煮着粥。灶膛里的火肆无忌惮,烧旺的火苗立刻反应到锅里,锅里的粥汤在沸腾翻滚,一直溢到灶台上,顺着灶台流到了地上,最后一锅粥变成了一锅不粥不饭的。为此,引来一顿责骂,我还挺委屈似地嘟囔着,不知啥时候才能摆脱烟熏火燎的日子。
用柴火鼎锅煮的粥,上面都有浓浓的一层油膜,其粥的营养都集中于此。小时候,我特爱吃这种油膜。用柴火鼎锅煮的饭又香又软,特别是锅底泛黄的锅巴,最好吃的就是刚出锅的时候,咬起来嘎巴嘎巴的,喷香,特别脆。弟弟总喜欢和我比谁咬的声音大,我们的笑声回荡在山里,能传出去很远。
烟雾缭绕里,看着锅里的米煮开花了,母亲就赶快将米汤舀起来,装在一个瓷盆里凉着,浓郁的米汤,大概是那个年代最高级的饮料了。

等听见饭粒细微的涨响声,有香气开始溢出锅时,把灶膛里的火退了,用余炭慢慢焙着。锅里的饭,慢慢收干水分,这样做出来的饭,又松又软。这可是一门技术活,火大了,饭就糊了,火小了,便吃不到金黄的锅巴。因此烧好一锅米饭,看似平常,却非易事。
那时正是身体疯长的时期,肚子饿得快,又没有任何的零食。有时候放学回家的早,菜还没做,奶奶偶尔会给先做上一份酱油拌饭充饥。奶奶揭开锅盖,水蒸气哗一下就散开了,舀一勺米饭在瓷碗里,倒上酱油,然后从瓦缸里舀一小匙凝固的猪油,米饭的热气迅速的把猪油融化了,油浸浸的泛着亮晶晶的光。柴火饭的清香和酱油猪油的醇香混合着,在唇齿间胶着,久久不散,不仅暖胃,还暖心。
奶奶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狼吞虎咽,问着我学校里的新鲜事儿,一个老人家,她所热切的,大概就是孙儿孩子的促膝围绕,家长里短。老人家渴望的就是这种温情啊。也许,每个人的成长都带着老一辈人的岁月。在那些孤独的岁月里,她的爱就像这碗酱油拌饭,一直伴着我,清香醇厚,绵远悠长。这种味道,一直到现在都让我念念不忘,却再未曾遇见。

小时候听奶奶讲寒婆婆的故事:传说掌管风雨、江河的神灵,兼司一冬冷暖,称寒婆婆。寒婆婆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孤寡老人,一生中尽其职为人类造福,却忘记自身温饱,终日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立冬后,天气日趋尽冷,必需取得柴火过冬。玉皇给她打柴的时间确定在每年的阴历十月十六,为眷顾她,每逢这日遇上下雨,寒婆婆会得到很少的柴火,而这年的冬天就会多晴日暖。如果遇上天晴,寒婆婆会得到很多的柴火,而这年的冬天就会多雨日寒。
奶奶讲完故事后叮嘱我们,不管天气如何,都要备柴过冬,不然到了天寒地冻,冷雨绵绵直落得人心慌慌,坐在家里骂天也没用。
阴历十月十六清早,奶奶一打开门,就会告诉我们寒婆婆有没有捡到柴。我在夜里会偷偷扒在窗户往外看,想看看寒婆婆到底长什么样,可一次也没有看到,早上还要跑到外面看柴少了没有。这种传说不知哄了多少懵懂无知的儿童少年,但这个自然现象对晴雨的判断还非常准确,我们也就乐此不疲地相信。

年龄稍长一些,我们结队几人带上柴刀,到大人们砍伐木头过后的山场,到处是枯干不久粗壮的树尾枝桠。手起刀落,只听“吧嗒”一声脆响,柴枝应声落地。山林里的鸟儿在歌唱着,砍柴的笃笃笃声在山谷里回响着,在这悦耳的声音伴奏下,不需多久,便砍得一堆结实的柴火。
这时讨柴火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挑那些不很粗也不很细的柴砍成一尺多长,装在竹制的柴夹挑回家。一种是砍成约一米长,用藤条或竹蔑捆成两捆,选一根较直的木棒削尖两头,插进柴捆担回家。再一种就是直接砍一根较粗的木柴,估摸着大概合适的重量长短,扛回家后再截短用斧头劈开。

秋天的山野,空气中都飘散着野果成熟的气息,有山楂果、鸡爪果、羊奶子、八月瓜、野葡萄、猕猴桃、米椎、刁梨果、野杮子、鼻涕果、山荔枝、山菠萝等,还有一些酸甜可口却又叫不上名字的果实。现在想起来,依旧馋得不行。砍柴之前,我们会先找这些“美食“解解馋,然后再急匆匆砍好柴,开开心心往回赶。一群小伙伴行进在崎岖的山道上,遥望着天边的火烧云,比较着谁的柴火好又多,就像现在的孩子比谁的玩具好又多。比完了,就使劲唱着快乐的歌。从坡上看去,场里的炊烟升腾起来,使劲抖一抖肩,脚步越发快了。

青山依依,绿水环绕。与山结缘的父辈们每次收工时,肩上都会扛一大根或是一捆柴回来,所以其他的老山兄弟姐妹们的家里总是堆集着很多漂亮的柴火,让我很是羡慕。
上五年级以上大一点的孩子们,需要到县城里住校读书。每到星期天的傍晚,尽早吃了晚饭,趁着天还没黑,在夕阳晚霞相映之下,孩子们就挑着几十百斤不等的柴火向县城出发,只见大一点小哥哥小姐姐快步如飞,小一点的小弟弟小妹妹踉踉跄跄地蹒跚前行。那时候的柴火卖价是八毛钱一百斤,卖的是良心柴,都是干透上好的硬柴,因为象酸椎、泡木一类的柴在讨柴时是不会要的。老山仔(妹)挑柴卖,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父母在单位上班,一周一天的休息日基本上都是用作打柴和兼顾打理菜园。家里人口又多,需要的柴火量不充裕。我体会到生活的艰辛,父母亲的不易,我就总是奋力地给家里尽量多打柴。自然,在那刀砍斧劈柴火的日子,手脚都留下许多的伤痕。
许多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去了,但是有些记忆经过了多少时间的磨洗也不会消失。多少次,梦中的我回到了小时候那一片青山脚下的小平房,一堆堆、一捆捆的杂柴,伴我度过了艰苦与快乐的童年。

一天,我在厨房,看着排列有序的煤气灶、电饭锅、电磁炉、微波炉等等,心中莫名涌起一种失落的情绪。我觉得这些东西仿佛是技艺拙劣的食物制造者,它们贸然闯入我们的生活,心急火燎地把饭菜做熟,便大模大样地以功臣自居,以为自己是现代生活不可或缺之物。其实,用这些东西做出的饭菜总是欠缺那么一种味道,一种温厚、香醇、质朴的味道。
柴火在灶膛里“哔哔啵啵”地响着,黑黑的铁锅被烧得斗志昂扬,那么烫。铁锅里的食物,“咕嘟咕嘟”地与旺旺的柴火呼应着,一派欢欣鼓舞。因为它们同根同源,柴火与食物彼此懂得,相互交流,它们用特殊的语言传递着关于美味的信息,协力完成任务,把食物的醇美味道发挥到极致。

很多人远离故乡后,反复怀念的就是炊烟的味道,有着深深的炊烟情结。很多作家写过故乡的炊烟,炊烟是柴火饭的象征,也就是家乡味道的象征。柴火饭是我们的味蕾上最初和最深厚的记忆,陪伴我们走过漫漫岁月。柴火饭喂养了我们的身体,也喂养了我们的灵魂,所以不管走到哪里,无论离开多久,我们都记得故乡的柴火饭,记得炊烟袅袅升腾的样子。游子的乡愁,也如炊烟一样,悠悠长长,不绝如缕。
那远去的柴火岁月,虽艰难而苦涩,却是多么温馨,有滋有味,心里是满满的欢快和甜蜜。那个年代的粗茶淡饭和原生态的美味,是伴随父母、兄妹浸染于血脉的亲情,刻骨铭心的记忆!在那悠悠的岁月里,那扛着柴火的大人和挑着柴火的兄弟姐妹,是我心中最宁静祥和的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