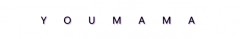2010年秋天,我到了眼下的住处燕丹村。
那之前的一段,我想去住地下室。一方面由于身上仅余几千块的资产,另一方面是遗憾没有这类经历,似乎缺了一块。
我去过几次地下室。
一次是在双井附近,去探望一位上访的大姐。顺着台阶下去,通道顶上横亘着热气管道,两旁是排列的小门,像是一个个储物间。
大姐住在其中一间里,一张单人床外刚够靠床头摆下一张小桌,桌上摆着电饭煲,床位摆一个案板和碗筷,其他东西都装进塑料袋,挂在墙上。
大姐说冬天不冷,夏天也不热。就是洗衣服有点费事,挂在廊道里阴干。
另外一次,是有个朋友来京住在建国门附近的地下旅馆,走下去以后像迷宫,拐两个弯才找到他住的房间,推开门是一副床炕,炕上铺的床垫横顶在门上,人要站在门外爬上床去,顶头墙上有一台九英寸的小电视。
我在网上搜了几间半地下室,打算去看其中靠近四惠的一间,又有点犹豫,这时接到了一个朋友将要退掉他在燕城苑租的房子,回陕西谋出路的消息,过去看了一趟,价格不贵,就放弃了继续寻找地下室的打算。
虽然房子没有装修过,但通透不缺阳光,我住的房间外边有两棵银杏树,叶子正在变得金黄,偶尔有一两片无声飘落。

房子离天通苑地铁站有五六站公交的距离,我第一次去赶上晚高峰,等公交的人黑压压排到马路中间,似乎调来全北京的公交也挤不下。
在新京报时做过一组报道,叫:《十万人困守天通苑》。不想今天自己成了其中一员,且走得更远。后来我坐了路旁吆喝三块钱一位五块钱两位的面包车。
上车之后,知道不是三块钱一位这么简单。
对面两条长凳座位,先上的人还可挨茬坐下,后来的在中间加小板凳,再后来的转不开身,近于被加在两旁人伸出的膝盖上,头顶车顶,车门最后是贴着人的脊背强行关上的,像是听说过的号子里塞人的情形。
车子开行,黑暗中人们看不见彼此,但听得清呼吸,关节和人体的旮旯彼此屈伸搭配,最大化利用空间。
有几位不知怎么替胳膊找到了缝隙,仍旧在看手机,屏幕的微光照亮了巴掌大的一片脸。
车厢外风声呼呼,感觉是一具夹心面包在运行,一旦翻车,只能挤压成肉泥,似乎在这条路线上的人谁也不在乎安全保障,把命交给了这个上车的机会和三块钱的价格。

房子实际在燕丹村地盘上的一个小区里,据说是当年燕太子丹的封地,也是供养死士荆轲的地方。除了一些附庸故典的对联,刺秦的往事自然渺无痕迹,但我在小区池塘边目击了一起刺杀事件,今天仍历历在目。
那天我饭后下楼,正待走进小区公园去散步,听到那边人群骚动起来,有人喊着杀人了,从公园那边跑过来两个警察,跟着一个小区老保安,在楼下观望。
老保安说是嫌疑人刚才从栅栏上翻过来的,不知上哪座楼了。
正在这时,一个男子的人影出现在对面三楼楼道,招手喊“我在这儿”。
两个警察立刻跑上楼去,过一会儿押着一个小伙子下来。
小伙子穿着白衬衣,经过我面前的时候,他的一只胳膊露着,从肘部到手指全是鲜红的,在阳光下触目,我想到了“沾血的手”这样的名词,但眼下不是沾血可以比拟的,没有什么可以替他洗刷,他显出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情。
后来知道,他是租居在村里的外卖小哥,刚才杀死的人是他女友。
女友提出分手后,他请求约在相邻的小区池塘见最后一面。见面时他准备了一把刀,当最后恳求无效后,他把刀插入了女友的心脏。
女友失血死亡后,他还在旁边坐了一会儿,被散步的老人发现,直到派出所的人到来,他才如梦初醒似的翻越栅栏开始逃跑,却又放弃了。

我没有看到他女友的遗体,公园封闭了几天。
再次开放时路过那里,地上还有褐色的斑点,心里一阵发瘆,似乎触碰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含有致命的禁忌,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
过了很久,这种感觉才渐渐消除,和地上的斑点一样被人遗忘。
这件事的流言也渐渐平息了,像是根本没有发生过,没有人关心那个青年的结局。
我想到他在阳光下被人挟持着走来,伸出那只洗不干净的血手,全然盖住了常年沾染的饭菜气味。虽然在耀眼的阳光下,却处在无法解脱的内心黑暗里。

小区北边有两大片田野,据说是燕丹村村民预留的回迁房地基,我初到燕城苑的那个秋天,它无所事事地开着大片的苜蓿花。
苜蓿花是紫色的,有点像豌豆,深得像是可以藏住人。花田中被人蹚出两条小路,成了我日常散步的路线。苜蓿田尽头是苗圃。有时我会有种不加价住到了公园附近的感觉。
秋深的时候,收割机开进了苜蓿田,田野四处飘散着新鲜草茬的气息,刈割过的草地空空荡荡,散落着从收割机后身断续吐出的草捆,在运走之前会晾上好几天,让我想到英国乡村草场的情形。
经过一个冬天的沉寂,春天苜蓿宿根自行发芽抽枝,开放花朵,引来蜜蜂嘤嗡和养蜂人在附近落脚,等待秋天的刈割。
这样周而复始的情形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年的秋天,耙地机的履带隆隆地开进了打草过后的田地,深深掘开泥土和其中的苜蓿宿根,打上了百草枯。
那一片田野被拉上了围栏,土地完全变为黑色,裸露深壕,似乎由富有生机的床铺变为墓坑,准备在处决后掩埋一群沉默的人。
准备去散步的我耳膜嗡嗡作响,感到我在这里的好日子似乎是结束了。
但日子仍旧持续下去。谜底揭开,春天田野里下种了玉米,玉米缓慢又按部就班地生长起来,在夏天的烈日下似乎面临焦枯,完全不像会有收成的样子,却终究在入秋后成熟起来,有了第一季的收获。
比起苜蓿田的开花来,不知算是有所得还是遗憾。

没想到我会在这座屋子里住了九年,直到电线老化,水管滴漏。
近两年酷暑,小区总是免不了短路停电,据说是有人私自给村里的门面接了电线。
超过负荷时,池塘边的电压器发出一声巨响,刺耳又难受,冒出一团火花后,小区顿时漆黑一片。
更多时候是跳闸,电工房只好安排一个人值班,随时跳了闸随时推上去,一晚上折腾数次。
2017年7月中旬的某天,晚上黑云低压,天空没有一丝光亮,闷热难忍,似乎世界就要窒息。
小区再一次短路断电了。
我从外面回来,看到小区大门口聚集了黑压压的人,堵住了马路要求解决问题,坐车前来处置的区委干部被包围在人群中,紧闭车门不敢下来,四周的人喊着说,“我们的老人小孩都快热死了”,他们在车里吹空调,有两个赤膊的人试图去堵住车底的排气孔,被家属拉住。
一会儿天空发出震耳的雷鸣,布满了奇怪的闪电,像是一个个首尾衔接的花圈,又像劈开大地的一道道创伤,瓢泼大雨随即洒落下来,似乎完全是黑色的,伴随着愤怒低沉的雷声。
大雨过后气温回落,临近窒息的人们总算感到了一丝清凉,小区的电力恢复,小车才得以脱身,一场群体性事件渐渐平息下去。

最初合租的室友离开之后,青来到了我的生活中。
当时她住在天通苑的一个群租房里。我去过她那里两次。
三室一厅的屋子里有十个人合租,青住在一个客厅的隔断间,有一个假窗户,一张床,床头抵着电脑桌,桌上有一部座机,她在这里打电话采访和写稿。
大白天屋里开着灯,光线完全透不到这里,我担心青骨头里的钙质会日渐流失。我把她接到了燕城苑的房子里。
我们在这里一起度过四年,后来青离开了北京,但偶尔还回来,再后来终究剩我一个人了。
我开始听一首花粥的歌《远在北方孤独的鬼》。
那些日子,我再次听见保安的自行车在窗下深夜定时经过。再后来装了摄像头,自行车的轮毂声才终于消失。
两居室的屋子无人合住,因为寂静显得有些大而无当了。
我感到自己需要一个充气娃娃。这是从一个朋友分享的文章引发的,文章的作者是他的中学老师,老师北漂了三年,用一个充气娃娃陪伴自己,临走时才恋恋不舍地将“她”扔进了垃圾堆。
虽然燕丹村里有成人用品商店,我还是按照偶尔听说的,从淘宝上订购了一个。
我让它在空下来的卧房里待了两天,才拆开包装。略一试用,我感到了后悔。
“她”只是一坨塑料,不管如何设计得像人的样子。

处置“她”成了一个问题。我不想把“她”扔进垃圾堆。感觉需要在田野上找个地方埋掉“她”,毕竟“她”陪了我一会儿。
担心土地坚硬,我另外网购了一套园艺铲。从前我希望购置一套农具,像有些居民一样在苜蓿田周边开拓一小块土地,撒上菜种,现在却是用来埋葬。
晚上我在田野上寻找了不短的时间,不知道在哪里挖坑好,思考着哪片土地至少在近期不会被翻动。
后来我选中了一片苗圃中两棵树中间的位置。如果人们移走树苗,看起来也不会涉及这里。
我挖了一个坑,把娃娃泄了气,手脚蜷曲地放入包装箱,有些委屈地埋了下去。
我以为这年春天“她”总算是安全的。但过了一个月左右,我一时起意去查看,苗圃已经大大变样,新挖了许多大坑,以前的树木被起走,新栽了一批树木,坑挖得比我想象的大很多。
我有点提着心走了一圈,没有发现娃娃的头,稍微宽心之余,发现娃娃的学生制服裙挂在一棵新的小树上,不由心里一沉。
再在苗圃周边打量,在荒芜的灌木丛里发现了两只塑料腿。看来是被挖掘机的利齿斩断,被工人抛掷在这里的。
我明白了,这片土地上没有任何一块地方属于我,不论是播种庄稼蔬菜,还是仅仅埋下一个充气娃娃。就像我住了九年的出租屋,并不会和第一天离我的关系更紧密一些。
这个夏天,也许我将离开它,再次迁徙。

作者:袁凌,本文摘自《在别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