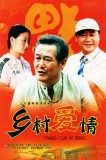【内容提要】进入新世纪后,以宏大叙事、语言杂糅为核心特征的大型主题歌舞,通过音乐、舞蹈、文学等艺术元素与多媒体技术的整合,以更有力、更丰富、跨门类的综合艺术表现形式,完成更为复杂的审美范式与文化形象的塑造。在世界范围内,大型主题歌舞以形式审美为话语形态,强调身体经验的同构与差异,超越了语言逻辑的隔阂,更易唤起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共情,使其成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与手段;其审美情趣及艺术形象一方面呈现出艺术语言自身的跨界融合、杂糅等现象,另一方面也以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形象,成为舞台表演形式“中国气派”的典型代表。借助比较研究的方法,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与理解大型主题歌舞这一艺术样式的审美特征、类型划分、文化认同等。
【关 键 词】大歌舞;宏大叙事;现实主义;类型范式;文化景观

大型主题歌舞(下文简称“大歌舞”)作为当代中国一种较为典型的表演艺术类型,一方面延续了中国传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形态,另一方面又借助现代舞台的艺术与技术话语完成宏大主题的叙事表达。进入 21世纪以后,大型主题歌舞已不仅限于“歌舞”的杂糅,更将杂技、情景表演、朗诵、多媒体、灯光技术等混杂于一体,以跨门类综合艺术表现形式,完成更为复杂的审美范式与文化形象塑造。在这一艺术样式中,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对抗与互渗,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博弈与平衡,构成了大歌舞的类型范式 [1]和文化景观。国外亦有类似大歌舞的综合表现形式,如爱尔兰的《大河之舞》、西班牙的《安达鲁西亚之歌》、黎巴嫩的《一千零一夜》等,同样以有主题的、大型的、综合的歌舞审美形式为话语形态,强调人类身体经验的同构与差异,在跨文化传播中更易唤起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共情,通过审美情趣及艺术形象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建构着国家、民族、地域的文化形象。

从艺术实践来看,大歌舞在艺术形式语言建构与类型分化层面存在着“跨艺术种类、跨艺术样式、跨艺术体裁” [2];在文化交流传播的层面存在着“跨民族、跨国家、跨文化” [3],由此,对其进行比较研究与分析既是对艺术实践的理论观照,同时也是学科建设的理论自觉。

一、异质共形的构建:大型主题歌舞的审美要义

较之歌剧、舞剧、戏剧、戏曲、杂技剧等艺术样式,大歌舞最鲜明的形式特征为“综合”,即将多种艺术形式整合于一个“主题”的表达框架之中,共同为主题表达服务。尽管歌剧有采用芭蕾为幕间插舞,戏曲亦有融入身段、纯舞,但始终以其艺术样式的本体语言为中心——声乐或“唱、念、做、打”为主要表现手段。然而,从《东方红》《复兴之路》这样的以“音乐舞蹈史诗”为名的主题大歌舞中可以看出,大歌舞的艺术样式构建是“去中心”后的“再中心”,即音乐、舞蹈、戏剧表演、朗诵等缺一不可,多种艺术形式综合营造同一主题的宏大意象,从而形成不同舞台表演艺术形式的异质共形,并显现出大歌舞独有的审美形式特征。

其一,“大”,即体量巨大,包括演员数量众多、舞台装置巨大等。如《复兴之路》以恢宏的气势在新世纪唱响中华文化的复兴: 3200名演员共同完成了一部作品,艺术地再现了从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直至 2009年之间 169年的历史画卷。大斜面舞台和大台阶的构成,“自觉地确立了两个美学空间的复调结构。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在两重天地间,史诗的品质兀地拔起” [4]。由此可见,以“大”为美是大歌舞最基本的审美形式特征,也是其有别于舞剧、歌剧、戏曲、音乐剧等其他大型舞台艺术作品的特征。

其二,“众”,即由多种艺术表现手段共同构成,是典型的跨门类艺术样式。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大型晚会,一般亦包含多种艺术形式,并由若干作品组合而成,但其单个作品的艺术形式较明确,如歌唱、舞蹈、小品等,且各作品形态独立。而大歌舞本质上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形态,其作品结构由若干篇章组成,虽然其中可能会涵盖若干首歌曲、舞蹈、朗诵、情境表演等,甚至某些歌曲和舞蹈曾经是成熟的独立作品,但是将其置于大歌舞作品之中仅能为其中的一个“片段”,如《东方红》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南泥湾》《飞越大渡河》等是传唱已久的歌曲,《飞夺泸定桥》《长鼓舞》《红绸舞》等也是成功的舞蹈节目,然而这些歌曲或舞蹈并不能完整体现整个作品的主旨。也就是说,大歌舞唯有作品的完整形态才能清晰传达其主题;与此同时,其中不同门类的艺术作品又有相对独立的完整形态。因此,大歌舞虽然是一种综合表演形态,但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形态。

其三,“全”,即作品体量巨大、视觉场面宏大,意味着大型主题歌舞的叙事方式大多趋于宏大叙事。虽然大型主题歌舞的叙事手法多样,甚至从小人物、从历史的某一细节切入,但是其“主题”或是包容地域多样性之宽宏,或是叙述民族历史之纵深,使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生成对某一历史、民族、地区的“全景式”审美认知。由此可见,大型主题歌舞的宏大叙事,往往建构的是对某一地区、民族、国家的文化符号系统,甚至在某一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建构起特定的艺术话语体系,即“宏大叙事往往是对自己所属的部落、民族或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发展历程和未来持乐观态度……宏大叙事可以是部落的、或民族的、或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种发展趋势的概括,今天的宏大叙事主要还是国家的或某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的产物” [5]。因此,大型主题歌舞的宏大叙事往往反映的是官方或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国家、民族、历史的整体认知,唤醒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

其四,“正”,即以中正、宏大为主要审美特征,其情感基调乐观积极,人物形象多为正面或英雄人物。这一审美特征基于宏大叙事以及体量巨大而生成。在这一审美价值取向之下,特定的人物形象、民族形象甚至角色形象往往会构成特定的审美符号,与宏大叙事结构下的部分形象构成具有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如以“国家—民族”为主题的大型歌舞,与单一的民族歌舞表演不同的是,其各民族风格的凸显不仅仅是为塑造单一族群形象,而是为唤醒与表达“国家—民族”的集体记忆,如《东方红》中彝海结盟时凉山彝族的形象,与最后一场民族歌舞时展现出不同民族的性格、气质等,都成为一代人对该民族的集体记忆:“在 55个少数民族中,几大民族在《东方红》中的位置凸显,极具代表性,同时又意味着国家的整体叙事中几大民族的重大意义所在……中国国家形象认同已经离不开少数民族如此的形象展示。”[6]这意味着大型主题歌舞已不仅仅局限为单一作品形态,而是一个塑造文化符号、民族形象的异质同形的审美场域,以更加有冲击力的艺术语言表达实现“国家—民族”的文化认同。
二、文化形象的差异:大型主题歌舞的类型滥觞
如前所述,大歌舞往往是塑造文化符号、民族形象的审美场域,当文化符号系统在宏大的叙事结构中展开时,一个以民族、以国家、以某一地区为单位的文化形象被建构起来。通过文化形象的建立与传播,大歌舞正以歌舞的方式使观众认识和认同特定主题之下的文化形象。从类型比较的维度来看,大型主题歌舞根据不同主题的性质,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国家话语表达的庆典型大歌舞;二是地域性、族群性文化展示的旅游演艺型大歌舞;三是特定审美风格彰显的艺术型大歌舞。

庆典型大歌舞是较为典型的以政治文化为主题的大歌舞形式,可以说是“乐与政通”的礼乐文明的延续,也是当代社会主导文化与精英文化结合的典型。在中国古代舞蹈史中,《大武》被定义为“是一个有诗、有乐、有舞、有特定主题的大型男子群舞” [7]。西周的制礼作乐,既为“王道政治”奠定了思想基础,更为后世礼乐文明提供了文化逻辑。 1949年 9月,为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华北大学文艺学院创作演出了 大歌舞《人民胜利万岁》。在现代政治语境中创作的《人民胜利万岁》,将传统民间歌舞元素进行提炼、整合与重构,以更适合现代舞台艺术的表演与欣赏,从而构建起鲜明的、崭新的国家形象,共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此后, 1964年《东方红》是首都音乐舞蹈界在“三化”座谈会后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5周年的通力合作,体现出“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文艺建设的重要原则; 1984年的《中国革命之歌》肩负着在“文革”结束后、庆祝新中国成立 35周年之间,如何重述历史、还原真实的使命,因此它被认为“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再现了历史的真实,既可以使观众得到审美艺术欣赏,又能从中受到革命传统的教育” [8],及至 2009年的《复兴之路》、2019年的《奋斗吧!中华儿女》,这些国家级庆典型大歌舞作品在艺术实践中构建并发展了“音乐舞蹈史诗”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艺术样式,既是对传统诗乐舞形态的时代发展,又与现代的歌舞剧、音乐剧等有所区别:诗化的叙事结构、复合的叙事语言、宏大的叙事主题。

旅游演艺型大歌舞突出的是地域性“风情歌舞”的审美特征,其消费文化色彩越来越鲜明。 20世纪 90年代,随着各地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充满地域风情的民俗歌舞成为新兴的旅游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深圳民俗文化村的大游行及民族歌舞演出,世界之窗所属的五洲艺术团将剧场与广场结合的大型歌舞表演等,为后来的旅游演艺型主题大歌舞奠定了基础。这种主题歌舞形式在进入 21世纪后“升级”为大型实景歌舞演出。 2003年,由张艺谋、王潮歌、樊跃一起合作的《印象 ·刘三姐》,集漓江山水风情、广西少数民族歌舞艺术及艺术家的想象力与创作力于一体,以远山近水、船歌月舞等视听奇观打造了第一部山水实景演出。实景演出的场域定位决定了其技术基础是大型的舞台装置及声、光、电设备,虽然突出的是“实景”,但其实主要依靠多媒体技术营造的审美奇观。《印象 ·刘三姐》不仅开创了“实景大歌舞”这一全新艺术形式的先河,更成为地方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种新范式。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颁布后,非遗热加速了这一类型大歌舞的生产。在旅游文化消费中进行本地域、本民族历史人物、英雄的宏大叙事,建构立足于本地域、本民族特色,又与当代旅游消费者形成共鸣的审美符号。从这一意义上说,旅游演艺型大歌舞一方面以“主题”叙事整合了零散的民俗歌舞以及民间文学单一叙事,具有了意义的完整性与审美的崇高感;另一方面其基于旅游消费的文化认同不免带有强烈的印象式、碎片化特征。

如果说旅游演艺型大歌舞是以“在地”为叙事空间,探索旅游消费场域下的文化认同,那么艺术型大歌舞则是以当代都市大众审美为基础,艺术形式创新为突出特色,以脱域为时空转换的现代化尝试。艺术型大歌舞文化形象的塑造不同于庆典型大歌舞所召唤的民族或国家认同,也不同于旅游演艺型大歌舞渗透着文化认同,而是更加追求审美感受差异的认同;吸引都市观众走进剧场的不是民族身份、文化背景,更多是对艺术性的向往,是剧场艺术可以引发的超越日常的审美体验。放眼全球,我们可以发现,成功的艺术型大歌舞如中国的《云南映象》、爱尔兰的《大河之舞》、西班牙的《安达鲁西亚之歌》等,不仅展现出精湛的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爱尔兰民族、吉卜赛民族的歌舞技艺与文化张力,同时也呈现出中外艺术的审美差异性及其由此产生的跨文化认同。

三、跨文化的共情:大型主题歌舞的心理映射
高质量、高水平的大歌舞往往会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具有标识性的“文化品牌”,获得广泛认可甚至在全球范围内都取得市场的成功。纵观全球,主题大歌舞作品往往在形式话语上更具特色,以形式审美为话语形态,强调人类身体经验的同构与差异,在跨文化传播中更易唤起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共情。如爱尔兰的《大河之舞》,其中踢踏舞技的令人眩目、女高音的余音绕梁、风笛的旋律悠扬,凝炼而清晰地传达出爱尔兰民族的气质,被誉为爱尔兰国宝级的演出。而大型原生态主题歌舞《云南映象》自 2005年推向海外以后,在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 50多场,创下了多个城市和国家演出市场的“票房奇迹” [9];《华盛顿邮报》以《超越〈大河之舞〉》为标题报道了《云南映象》在美国表演的盛况,称“中国创作了一部像爱尔兰踢踏舞一样阵势壮观的民族舞蹈” [10]。

不同文化背景的大歌舞之所以能有效、广泛地完成跨文化、跨地区的国际传播的重要原因在于:音乐与舞蹈的非语言性可以超越语言的鸿沟与文化藩篱,其形式之美直达人心。这是大歌舞相较于其他艺术形式跨文化传播的优势。从表演形态来看,大歌舞能整体、多层面地调动歌、乐、舞、朗诵等多种手段表达主题,也可以更好地融合多种审美形态及文化风格。如中国东方歌舞团的《东方之爱》,以两位即将喜结连理的年轻人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与探索为叙事线索,将五大洲十个国家的风情歌舞串连一起,“以爱的名义领略世界风情” [11];黎巴嫩的《一千零一夜》,将西方的芭蕾舞和现代舞融合在阿拉伯舞蹈中,讲述文学名著中的爱情主题,展现千年文化的交流。因此,就形式之美而言,艺术型大歌舞在跨文化传播中有着显著的优势,更易获得全球演出市场的成功。

以形式特征为切入点,以超越日常的审美唤起观众的共情,从而达到民族或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审美认同,这是主题大歌舞在跨文化传播中获得成功的一条重要途径。而观众所共之“情”,其出发点往往来自审美上的超常体验。不论是《云南映象》中“杨丽萍式”的灵性之舞,还是西班牙《安达鲁西亚之歌》中弗拉明戈的烈焰燃情,在跨文化传播的心理映射轨迹上,诉诸审美的、直觉的形式话语是基础,即大歌舞所构建的文化符号应能唤起人类的共同审美感受;而基于形式之上的作品意象则在整体的宏大叙事中凝练、典型地体现其国家、民族、地区的文化形象,这一文化形象既是印象式的,又是概括性的;既有鲜明的、符号性的特色,又存在多层而多维的诠释空间,留给观众无限回味之余地。

结 语
以宏大叙事、语言杂糅为核心特征的大型主题歌舞,作为当代中国舞蹈的一种艺术类型与美学风格,通过音乐、舞蹈、文学等艺术元素与多媒体技术的整合,以更有力、更丰富的、跨门类的综合艺术表现形式,完成更为复杂的审美范式与文化形象的塑造,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一种艺术话语。其审美情趣及艺术形象呈现出艺术语言自身的跨界融合、杂糅等现象;而其以形式审美为话语形态,强调身体经验的同构与差异,则可以超越语言的隔阂,更易唤起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共情,从而成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与手段。

今天,中国面临着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建立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重要任务。对外文化传播的话语生态中,既有国家政治层面的语境,亦有附着于商业、社会交往语境下的文化交流。在跨文化交流中,“语言”是重要的工具,然而纵观全球歌舞艺术的传播图谱,歌舞艺术以其形式审美之特点,超越了“语言”的巴别塔,可以更好地唤起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文化共鸣。对于大歌舞这一艺术本身,需要更多的跨界合作,共同研究、共同创作,进一步探索其形式逻辑与规律,而并非仅仅停留在不同艺术形式的组合,甚至可以突破现有艺术门类之藩篱,寻找更有效的、适用于大歌舞的艺术表现形式。而艺术界也需要看到,原先研究视野中处于“边缘化”的大歌舞,不仅仅是政治话语的体现,更是文化符号及经典审美意象构建的重要场域,往往能带来更为深层而广泛的文化认同和审美认同。作者:仝妍,黄际影

【注 释】
[1]吕艺生将大型晚会分为六种类型:庆典性晚会、节日性晚会、纪念性晚会、行业专题性晚会、文体性晚会、景点旅游性晚会。参见吕艺生 .大型晚会编导艺术 [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4:16-21。日本美学家竹内敏雄根据艺术创作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的区别,将全部艺术类型分为种类类型与风格类型两大系列(参见〔日〕竹内敏雄 .艺术类型论序论 [M]//竹内敏雄 .艺术理论 [M].卞崇道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大型主题歌舞既有艺术种类(体裁)系列的类型特征,同时也有艺术风格系列的类型特征。
[2][3]彭吉象 .比较艺术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范围 [J].艺术评论, 2020(1): 13,16.
[4]张华 .创造者张继钢 [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1:127,135.
[5]王加丰 .从西方宏大叙事变迁看当代宏大叙事走向 [J].世界历史, 2013(1): 5.
[6]王璐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少数民族形象表述 [J].民族文学研究, 2012(4): 67-68.
[7]袁禾 .中国古代舞蹈史教程 [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4:18.
[8]王克芬,隆荫培 .中国近现代当代舞蹈发展史( 1840-1996)[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9:180.
[9]王立元 .杨丽萍:用灵魂舞蹈 [N].中国文化报, 2014-01-21(001).
[10]王珍 .杨丽萍:孔雀飞过 40年 [N].中国民族报, 2018-12-28(09).
[11]王立元 .《东方之爱》:以独特的方式诠释“爱” [N].中国文化报, 2015-11-1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