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候是1986年盛夏的一个午后,阳光正好。我和几个小伙伴相约到村南大坑玩水,大坑直径100米左右,由于多年取土形成。每到夏季便积满雨水,最深处达五六米深。我们经常去那里野浴,因为有溺死的先例,家长对我们看管很严。回来只要指甲挠我们的皮肤出现白道就是一顿暴揍,末了还扔下一句:“再去,摘了你嘎拉哈!”此处画重点,读音galaha。
嘎拉哈又称羊拐,源自满语。是羊的后腿膝盖骨,一副为四个,是北方(尤其东北)小女孩的玩具,以小羊拐为上品。

现在想想,那年我的同学刘某江野浴真被他爹摘了嘎拉哈就不至于死掉了。他后来脚划破了还偷去南大坑洗澡,那里水质浑浊,经常有烂掉的家畜的尸体,他感染了破伤风,在去省城求医的途中过世,想来令人不胜唏嘘。
回到正题,羊嘎拉哈四个为一副。玩嘎拉哈,都是要一副嘎拉哈配一个口袋的。正面像人的肚脐眼儿叫“坑儿”,背面像胖人的肚皮叫“背儿”(肚儿),侧面像人的耳朵叫“轮儿”,还有一侧什么都不像就叫“真儿”。在东北称为“歘嘎拉哈”,一般都是在火炕上玩。

东北的火炕和炕席是绝配。这种席子多用高粱秸秆或芦苇秸秆的篾条编成,好一点的还有竹篾编就的,一般人家是用不起的。这种席子冬暖夏凉,便于擦拭。你设想一下,隆冬时节,窗上结着冰凌花,几个孩子围坐在炕上欻嘎啦哈,那是何等温馨的画面!但这席子时间久了会有断裂的,光腚娃娃的小屁屁是要被划破的。炕席已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只有在民俗馆才能看到,每一根斑驳的篾条都写满了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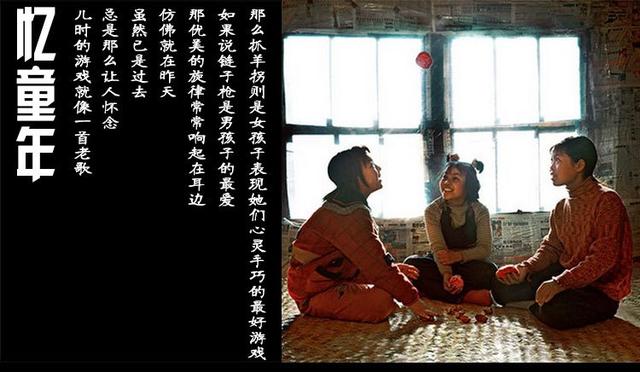
歘的过程是这样的:用一只手(另一只不用)将四个嘎拉哈散乱地抛在炕上或桌上(一般都是在火炕上)。然后将口袋向上扔起,在口袋落下的时间内将四个嘎拉哈都先搬(以下的过程叫搬)成真儿,用手抓起,再接住落下的口袋(用同一只手)。如口袋和嘎拉哈都没有落在炕上,则接着搬下个背儿,依次接下的次序是坑儿,轮儿。最后,把口袋抛起,手把都成轮儿的嘎拉哈抓起。如果口袋落下时在手里(没有落在炕上)则第一个回合完成。倘若在搬的过程中口袋没能接住,东北话就叫“坏了”,交由下一个人玩(抓)。其输赢的判断是:在搬四个嘎拉哈的过程中,谁抛口袋的次数最少,谁就是赢家。这只是歘嘎拉哈的一般过程,当然里面还有许多技巧。比如说:在搬真儿时,因为下个是背儿,所以将真儿一字排好,到搬背儿时用手心一压就行了,节省时间和次数。歘嘎拉哈的输赢关键,一是口袋要抛得高(留空时间长),二是抓的过程要快,尽量用少的次数完成全过程;这个游戏要手、脑、眼并用。
那时常见的玩物还有弹弓。

这是简陋一些的,最常见。

这是精致一些的,需要大人的帮助才能做成的。
弹弓 ,七八十年代开始流行。弹弓一般由弓架、皮筋、皮兜三部分组成,一般用树木的枝桠制作,呈“丫”字形,上两头系上皮筋,皮筋中段系上一包裹弹丸的皮块。弹弓的威力取决于皮筋的拉力和皮筋的回弹速度,皮筋拉力越大能匹配更重的弹丸,皮筋的回弹速度越快能提供给弹丸一个更大的初速,弹丸越重、初速越高威力就越大。
那时物资极端匮乏,做弹弓最难弄的是皮筋。拉力和回弹速度最好的是自行车内胎和气门芯,但很难找到,自行车内胎都是缝缝补补又三年。安北站前修车老头没少受到我们的骚扰,估计在偷了他的自行车内胎时骂得最多的是“摘了嘎啦哈”。现在想想怪内疚的,愿你在天堂修理更多的自行车。
一年夏天,我和伙伴们到菜园去偷瓜,朗日高照,只能匍匐前进,因太过专注路面,护园老头朱老六已经直直地立在那里等着我们呢。末了是朱老六将此事告知家长,家长无外乎是打断腿摘嘎啦哈的骂语。伙伴刘某柱顽劣至极,决意报复朱老六,趁其午睡用弹弓将其玻璃打碎。怀疑我们又苦于没有证据,见了我们只能碎碎念念地骂着。
那时还没有保护野生动物一说,我们就用弹弓打鸟。我同学吕某东,他用弹弓打鸟很少有失手的时候,我相信他要是参军肯定是名优秀的狙击手。打了鸟之后需要生火烧着吃,没有任何佐料,那味道至今难忘。
对于影像的记忆只有黑白电视了
记不得村里什么时候通了电,我的记忆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盲点.后来我问了父母.确认是在我儿时.几年之后有了电视,是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我遍寻了大脑的储存,好象都是熊猫牌的.最初村里只有几台,我老爷是大队书记,他们家是最先有的.因为电视少,所以到了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场面相当壮观,就像看电影一样,炕上坐了满满的人,地下凳子不够了,就用砖一垫,横上一块木板,并排挤了很多人.人们都目不转睛地着这个新奇的东西.

我们小孩是最活跃的,能一直在人家把电视盯到再见,最后才被大人几次三番地扯回家.关于电视还有个有趣的事,村里有个朱大爷,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他是村上打米厂的电工,腿有残疾.打算要买电视,很多人让他买十四寸的,他不同意.他说我买就买十七的,十四的看不着脚.当时乐晕了一批人.是的,这种单纯的快乐来自心灵的简约,刻意而为的简单生活难登其境.
那时的雪是真大。当傍晚时分零星的飘起了雪花,大多数的情况下第二天会大雪封门.真是如此,直至今日,我记忆里的那个时代都是冰天雪地的.在村子南面的场院里要是下了大雪,往往要堆积得一人来高.很多人家早晨开门会费很大劲.一旦来了一场大雪,我们几乎不堆雪人,这种柔柔的东西我们来不得.拉雪爬犁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

村中间有一条东西向宽道,我们拉着爬犁来回地奔跑,看谁的速度快.或者两个人石头剪子布,输的在前面使劲地拉,赢的洋洋得意地坐在上面,尽管冷风如刀,但乐趣不减.偶尔会有谁家的狗在旁边跳跃跑动.可是坐着的不要太过高兴,说不定快到终点的时候,拉爬犁的猛一用力,便会掀翻下来.玩饿了就回家拿了冻豆包啃着.手脸被冻龟裂了,但却冻出了健壮的体魄.很少听说哪个孩子感冒了吃一片药.而现在很多被厚厚的羽绒服包裹的孩子却孱弱得很?现在村里的路已经铺了水泥路,每当我回去看着这条路时,心总会莫名的痛.水泥覆盖了路面,也覆盖了一段记忆.
我是一个怀旧的人,还有很多儿时的故事如在昨日,譬如村中的一口老井,以及汲水的长长的队伍.譬如生产队里的马厩,以及打更老头的胡须里的故事……我终究是一个走不出的人,而时间的不可逆注定了有些东西是要废弃的.但我也并没有因此而感伤,我常常在想,那无非是一段流逝的时光,包裹着一层温暖的色彩,在北方旷远的空中逶迤游走。它穿越荒村,穿越小城,它盈盈带笑拂拭我的心田。
码字不易,最后献上本人“玉照”一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