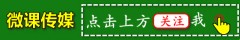北方的冬天,一到晚上六点,外面就一片漆黑、行人稀少了。
吃过晚饭,我习惯性地拿起电视遥控器,将所有的频道调了一遍。之后,又拿起手机刷起来。应该承认,如今的传播媒介多样化,内容更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目不暇接,可我却总想找点更引人入胜的东西看。有时候,我不免会反思,自己的口味怎么这么高了,想想小的时候,那些没有手机、电脑、电视、甚至是收音机的日子,尤其是晚饭后至睡觉那段时间,自己是怎么过的,夏天倒还有些趣味,能饭后趁着天色尚明跟小伙伴们打闹一番,而在冬季那三四个月里,除了腊月二十三小年至元宵节这二十多天里,能够与小伙伴儿们出去放放鞭炮,悠逛几回外,其余那百十来天的难捱日子,都是怎样过来的?
于是,便回忆起七十年代末、自己还是八九岁的孩童时,那一个个漫长而又枯燥的冬夜……
仔细回想,那个时候的闲暇时光虽缺乏色彩与趣味,却并不是一片空白,它一直在我的心底深处牢固而又沉甸甸地占领着一席之地……
那时节,入冬后,一到天黑,街道上、巷子里,就会弥漫起浓稠的大雾,那雾气灰蒙蒙的,将一家家分割起来,让每一家的庭院似乎都成了一座孤岛,让我们这些只能猫在家里的孩童心头沉重,困惑、烦躁却又不知所措。
晚饭后,一家人就待在只点着一盏嘎斯灯的屋子里,坐在刚做完饭后、余温尚在的热炕上,相对无言。
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嘎斯灯时而浸入一些水后吐出一连串气泡时的噗噗声。
巷子里也是静悄悄的,除非有推着自行车卖酱豆腐的小贩经过,会发出一声高亢激越的吆喝:酱豆腐——臭豆腐——辣豆腐——
我喜欢听那一声嘹亮、苍凉而又带些悲壮韵味的吼声,那声音初听就如一根被莽汉奋力抛到半空去的棍子,旋转着……抖动着……呼呼有声,韧劲儿不绝,穿透力十足。随着这一声声的吼声响起,我的思绪能够追随着它在天空中像蝙蝠一般游荡。即使是叫卖者越走越远,声音逐渐微弱,乃至消失。那余音竞还如一根游丝,在耳洞内久久萦绕,牵引着我的神思。
过了很长时间后,叫卖的小贩彻底走远了,能让我们这些孩子唯一关注并产生新鲜感的来自外界的的声响也彻底消失了。
想想距睡觉还有一段时间,百无聊赖之下,心中不禁会产生一股难以言说的无奈和寂寞。
在炕上躺下坐起,扭过来扭过去,如坐针毡般地耗了一会后,我终于忍不住,起身跟大人说,想去邻居家听会儿收音机广播的评书,得到的回应却是:不可以!
大冬天的,这么晚了,不许去!
于是,我只得撩开炕被一角,拿出那本唯一的、前后都少页的小人书——《洋葱头历险记》,凑到灯下,潦草地翻弄起来……
翻弄了一会儿,我又拿出半块吸铁石、一根穿了尺把长棉线的缝衣针,趴在炕上的小木方桌上,自得其乐地玩起来。我用手捏住棉线的另一端,提起来,将针悬到吸铁石上面一两寸高的地方,然后,左右晃动手臂,看着那根针,不论我的手歪到什么角度,都会不坠下来,那针尖奋力地想要挣脱棉线,扑向吸铁石。于是,这个不解的谜题会让我继续新奇好长一段时间。
熄灯后,睡前躺下时,我不禁会幻想起自己生活在城市中的情景:宽敞的马路,明亮的路灯,一家家闪着五颜六色霓虹灯招牌的商铺……当然,这些场景都是在电影中见到的。带着这个幻想,我进入了梦乡……
深冬到来了,入夜后,北风呼啸,吹得院子里那些光秃的树枝咝咝嗖嗖作响;吹得房顶上的烟囱像哨子发出低沉的呜咽;吹得堂屋的两扇木门发出吱吱呀呀地痛叫;吹得院子里扣在存放着窝头与冻豆腐的大缸上的铁锅发出咣咣铛铛地震颤;吹得北窗户上钉的塑料布时鼓时瘪;吹得我的心头就像是一片荒芜的沙地扬起泛泛的沙土……
我喜欢这猎猎的北风,毕竟,它能带来远方的某种讯息。
熄灯后,洋炉子里刚填进去的废旧柳条筐枝条燃烧时会发出爆竹般清脆的响声,窗外,猫头鹰偶尔会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这时候,躺着被窝中的我会想起那杳无人迹、枯草瑟瑟的荒野,会想起一轮凄凉的冷月照耀下的黑黝黝的冷杉树林,我仿佛看见,在那个地方,有一头狼,或许是一只狐狸,正夹着尾巴,孤独而又左顾右盼地走着……而我的心,就在它身后的不远处,如一个蹑手蹑脚的跟踪者,屏住呼吸,跟随着它……
带着这个幻念,在昏昏沉沉之中,我缓缓地进入梦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