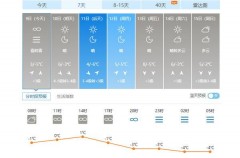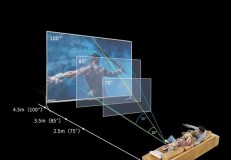”全新,有碎钻,非常漂亮,包邮不讲价”,宋羽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将自己的粉紫色钻石项链打六折出售。宋羽是一个26岁的北漂,她告诉南风窗记者,自己在疫情期间 “每天脑子里都在不停地想,想着怎样更省钱,想着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卖。”
在国内最大的二手交易平台闲鱼上,每日都有人出售各式物品,但最近一个词条明显多了起来,“离开北京”。
“因离开北京,甩卖一次也没用过的健身卡”、“由于疫情原因离开北京,急售电子琴”、“准备离京返乡,免费送猫”。《南风窗》统计,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闲鱼上超过800个新增数据与离开北京有关。
卖掉这些东西就离开北京。选择离开的人原因各不相同,有人因为工作调动,有人因为伴侣,更多的人是在新冠疫情下陷入低迷,清空掉带不走的、不愿意带走的物件,向北京道别。
真正穷,顾不上精致2月1日,正月初八,回老家过年只待了八天,宋羽就赶回北京。当时,新冠疫情还在风口浪尖,她却相信,复工的日子即将来临。“回来还要隔离十四天,万一这期间幼儿园突然开学了怎么办?”
复学的日子,一拖就是三个多月。她的幼师同事们有的回北京后,又重回家乡等待开学。很多则在朋友圈里有了自己的副业,还有的已经转行,到社交平台做电商直播。
等待中的宋羽要坚持不住了。所在的民办幼儿园失去了学费这一主要收入来源之后,每个月发给教师的,只有1000元左右的薪资和600元的房屋补贴。

月收入腰斩,迫使她”脑子里每天都在不停想事情”,“怎么样可以更省钱”。疫情期间的四个月,她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和化妆品,这在过去不可思议。作为时下流行的“精致穷女孩”,这些年她的消费观一直都是——即使钱不多,人也要为了自己向往的生活和喜欢的东西变得精致。
“其实这能害人”,宋羽如今却这样评价“精致穷”。
疫情之后,她因为没有存款,对生活风险的抗压能力几乎为零。以致现在常反思自己,“当初应该不买它们,应该把钱攒起来”。
“把所有能卖的都卖了,”为了交上房租和还清花呗,2月底始,她开始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卖东西。先是蔻驰、香奈儿等名牌包,再到新换滤芯的空气净化器,接着卖欧美大牌眼影盒和意大利鞋履品牌的千元礼券·····
两个月间,她陆续卖掉了很多“身外之物”。连平日她最心爱的、朋友送的生日礼物——香奈儿护手霜也被她挂上闲鱼,最后以300元的价格成交给另一位“精致”女孩。

“情况不允许我精致,还是好好生活吧,”她告诉自己。
可还是撑不住。即使比从前月开销减少近百分之八十,2000多元的房租依旧让她捉襟见肘。她有要坚持的原则:山穷水尽也不能向家里要。宋羽说,“工作多年未帮过他们太多,现在不能让他们知道我连自己也养活不了。”
为了凑房租,4月初,她到便利店打小时工,时薪17元,从上午7点上到中午11点,一个月能挣近2000元,下午她再回家继续上幼儿园的直播课。
在北京的第八年,这是宋羽第一次觉得要“承受不住了”,“无论是在身体还是心理上”。在过去,她一直认为这座城市代表希望和梦想。18岁从职业高中毕业,她只身一人来北京从事幼教业,从未想过离开。
“从前生活太丰富多彩了,快乐一天算一天,”宋羽形容。而现在的北京更像是梦,梦有要醒的一天。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房东催租的信息。
4月30日,她给房东转账后,躺在床上看着手机屏幕上弹出的余额提醒短信,突然发现自己,“辛苦挣钱一个月,一分不剩。”就在那一刻,她感到“没有希望了,挣的钱都给房东了”。重新开始是她在现实下唯一的选择。
5月初,宋羽开始在闲鱼上甩卖出租屋内还算新的电器、家具、食物及舞蹈课的年卡,并在每条商品的介绍上打上“离开北京”的简介。她说,“岁月静好的时候买东西是开心的源泉,遇到事情,才懂得家人说的道理。”
“想哭却已经没有眼泪”离开北京,不是一个新鲜词。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2153.6万人,比2018年减少0.6万人。其中自然增长人口数量达5.66万。换句话说,北京市在过去一年里净流出6.26万人。
今年受疫情影响,北上广等超一线城市,GDP全部同比下降超过6个百分点,工业、投资、消费,包括房地产成交率也几乎全部同比下降。更多的“后浪”选择流出北京,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与宋羽一样,在北京呆了8年的深圳人墨墨也打算离京。
墨墨是一家2018年底成立的艺术培训机构创始人。受疫情影响,该机构四个月未能开学授课,培训场地月租3万,教师工资2万多,自住房租4000元···都是他每月需支付的成本。月底要交租金和付员工薪水时,是他最脆弱的时候,“像是在扔钱,心在滴血。”
5月初,等待了近四个月的复工通知无望后,他认为“基本上不太可能了”,打算再等最后一个月,再不复课就遣散员工离京,及时止损。
他还没有将即将放手不做的想法告诉员工,却将放在出租屋里自用的雅马哈牌钢琴摆上了闲鱼。原价7000多元、七成新的钢琴最终以2800元的出售给了位“爽快的买家”,现在只差“货拉拉上门拉走”,相当于是“贱卖”。

“我已经没有什么不能舍弃的了,以前还会放不下在北京积累多年的资源与人脉,现在一切都无所谓了。”他说。
2012年到北京市某高校钢琴系上学,从读书始,墨墨就到校外机构做钢琴助教,随后升任老师,毕业后当上了店长,两年后“出来单干”。
“学音乐的,都会想红,想在圈子里小有名气,”这是他留在北京的初心。2019年底,他感受到自己的培训机构要“起飞了”,旗下授课学员增到了100位,“年后打算大干一场!”
而疫情给一切按下暂停键。原本很有前途的培训机构,现在随时可能资金链断裂。残酷的现实让他在过去四个月里情绪崩溃了很多次,“想死”的心都有了。看着过去的积蓄累月递减,他只能“每天吃了睡睡了吃,打游戏,偶尔弹弹琴”,其他的“什么也不会做”。
“现在还没到最后一刻,也许奇迹就发生了呢,” 他曾多次这样告诉自己。

5月13日,期盼已久的北京市复课的通知终于来临。通知显示,北京市中小学生最早可于6月1日复课。不过,该通知最后提及,校外培训机构复学时间另行通知。
即使奇迹发生,6月培训机构能顺利复课,墨墨依然下定决心,“再撑两三年就回深圳”。回老家之后,他可能会去考公务员,“陪伴家人是最重要的”。
今年4月,墨墨在深圳的奶奶因病去世。正月初七就回京的他没有见到至亲的最后一面,深受打击的同时,他却发现自己内心麻木到“想哭却已经没有眼泪了。”
又一朵后浪离开北京5月10日,河北邢台青年张少川在闲鱼账号上新了8个物件。从烤面包机到情侣枕头,这些商品是他“又一朵后浪离开北京”的标志。
他还打算将养了一年的猫转让出去,“不是因为不好带,而是他只属于北京。”
张少川觉得自己不属于北京,他打定了主意要“净身”离开,就像当初什么也没带就来了。

2018年,他辞掉了家乡县城国企的工作,接受了一家北京某新媒体的offer。大学一毕业就回小县城工作,他多少有点不甘,有了这份工作,他立刻来了北京,“即使它只给我2000元月薪,我也要来。”“我想做有影响力的青年,用文字养活自己!”
张少川在北京工作得不错,一个有着几十万粉丝的微信公众号,运营、内容、涨粉最后均由他一个人负责。但是繁重的工作任务,让他一周七天都只能呆在逼仄的出租屋内,周末也在准备要发送的内容。
北京这么大,可是张少川的活动范围甚至不如他当初在县城时来的大,“很讽刺是吧?
呆久了,他开始觉得自己过上了一种“双脚离地”的生活。他每天在公众号上写东西,“我关心风,关心蝴蝶,我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爱情。”但是实际上,他关心的都只是工作,而没有生活。

这样的感受一到过年回家时尤为明显。认真工作一年,他总认为自己进步了很多,但一接触到家人和朋友,他发现自己格格不入,“他们只关心酒关心烟,关心你谈婚论嫁的对象。”张少川在北京没有获得成就感,在老家也没有归属感。
回家,可能是悬挂在每个北漂头顶上的一把剑。2020年的疫情,加速了张少川的回归。
在家远程办公了四个月,他在网络上见证了2020年初各国发生的生离死别。而老家稳定的一日三餐、家人陪伴,让他反思,自己一个人在北京过得多么没个人样。而此前家人一直提起的,“安安稳稳地生活,比如说当中学老师”,挺好的。而在此之前,中学老师是他曾经最讨厌的工作
“这不是对生活的妥协,真实的人间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需要去了解他,学习它”,他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廉思形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当代青年成了“战疫一代”,更是对青年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90.1%的受访青年表示,“疫情期间,我更加理解父辈们的思想观念”,新冠疫情让代际间价值观的隔阂有所缩小。
“我就是想回家了”,张少川说,“想去感受真实的人间了。”
在疫情期间最困难的时候,墨墨在单曲循环一首歌,歌词里唱到的”茶包渗入家里,村舍候鸟歌唱,吃妈妈一片姜,有爸爸讲理想。”他现在觉得那就是最理想的生活。
(部分受访者采用化名)
作者 | 朱秋雨
排版 | 阿丽菜
南风窗新媒体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