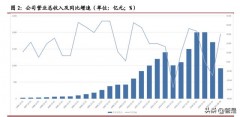原创 人物作者 人物

许巍的音乐里总有一种脆弱的力量感,它不愤怒,也一点都不激昂,最后一个字的唱腔总是向下滑,悲观的生活和旺盛的希望,他同时承认。
文|马拉拉
编辑|萧祷
摄影|王文
造型|孔宇
背景音
见面那天,许巍迟到了。
透过工作室门前没有什么别枝的盆栽,可以看到许巍来了,走得匆匆。相比以前,他的身上开始有了肌肉的线条,皮肤少了暗色的斑点,头上的抬头纹也逆向地被时间抚平。这次拍摄的服装是他自己挑选的,这两年他开始研究潮牌「臭美」,买了一圈,也交了不少「学费」。
「抱歉,我知道今天有工作,之前有准备的,结果昨晚上一拿吉他,完了,早上五点钟还在那弹琴。」许巍用没有很重的力道去握曾拍过很多明星人物肖像的摄影师的手,再双手合十。他已经化完妆,头发里有亮粉,然后,他要把自己交给镜头,短暂成为「明星」许巍。

想要获得许巍的消息没有那么容易,他没有微博,没有个人平台,从2008年开始,他拒绝综艺,拒绝颁奖,拒绝宣传通告,接受很少的采访。网上搜索他的资讯,14页到底,整整齐齐。有粉丝实在想知道他在做什么,跑去曾合作的键盘手臧鸿飞微博上问,在吉他手李延亮的微博下蹲。
他现在的工作室,在北京四、五环之间的文化园区内,两层小楼里最大的空间给了录音室。那里还有阳光可以通过落地窗洒满房间的书房,和书房平行的楼梯间种了很多植物,颜色沉绿。这栋原木色的建筑和他给人们的感觉有点类似,并不光鲜,具备一种被藏起来的温柔感。
录音室里,「明星」许巍要完成3组拍摄。第一组是拿着吉他弹琴,他能一边应付镜头一边和旁边的乐器老师聊天。第三组是清场之后「自己玩」,完成度更高。只有在第二组,手摆在吉他上不能随意拨弄的时候,拍摄卡了一下,他找不到合适的目光落点。那是仅维持了三两分钟的沉默,摄影师按着快门没有说「好」,旁边一直给他信号的工作人员没有抬头……许巍像小孩子哪里做得不好一样,抱歉地笑了,「是有点僵哈?」
他还是很敏感,不管是被别人对待,还是去对待别人。新专辑《无尽光芒》的巡回演唱会上,每场总会有一些怀有身孕的准妈妈在台下观众席中,许巍有些担心,「6、7个月肚子已经很大了,我都害怕紧张,害怕谁把她挤一下。」所以大家有了一个不成文默契,如果准妈妈的座位是靠前的,就帮忙协调往后面坐,如果还是想靠舞台近一点,那她们会得到一堆用来盖住肚子的毛巾。舞台前面有返听的低音音箱,许巍觉得太震了。
有一些粉丝会追着演出跑,所以这些年里许巍跑商演,从来不会周六和周日连续,更不会一天接好几场,「赶路的时候,心态是很奔波的,不管台上台下都很难很踏实投入到现场的演出。」工作人员向《人物》透露了原因。
「听他的歌,觉得他像是你小时候背着你的那个大哥哥。」一个听众在许巍的歌曲评论区这么写。
不少人听许巍的歌会被感动。2012年《此时此刻》之后,他带着自己的团队去了一趟英国,在甲壳虫乐队演出过的洞窟酒吧,他表演了几首歌,下面一个男生用双手捧着自己的脸,哭了。他和许巍一样是西安人,从15岁开始在曼联参加青训,后来膝盖受伤了,非常严重的伤病,停顿的两年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是《蓝莲花》和《故乡》陪着他走出抑郁。那天他坐了6小时的车去见许巍,路上弄丢了自己的钱包和护照。许巍抱了他,把常穿的蓝色卫衣脱下来当礼物,在上面很工整地写:「祝你以后越来越好。」
现在也是这样,不管粉丝要求写在最普通的本子上还是自己的专辑上,他都一笔一划地写。同样,听众也很认真地在歌曲下面写自己的故事,「活了36年,庆幸自己还活着,感恩自己有好多人爱着。直到8天前才知道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很幸运地找到了亲生母亲。」像是一个树洞。他总是在人们踽踽独行的时候被想起,曾经随意和路上一个司机聊过他,是经历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摇滚鼎盛时期的北京人,他说自己以后可能不会去听那时候其他歌手的演唱会,但还是想去看一看许巍,「听他的歌你不会觉得他唱得好不好,你会想起一些自己的事情。」
就算没有新闻,许巍这两个字也曾经和明星联系在一起。2003年,陈奕迅和孙燕姿正当红的时候,许巍凭借《时光·漫步》拿到了音乐风云榜那年除了「最佳新人」和「最佳女歌手」的所有提名。设置摇滚单元的元年,5个奖项里,他拿了3个。后来崔健,窦唯,郑钧和汪峰陆续拿奖。那年《蓝莲花》是「内地十大金曲」,对这个名词最简单的一种解释是,许巍把摇滚唱出圈儿了。
有媒体曾总结许巍的粉丝主要是都市小资白领,但实际上远比这个范围更大。打开QQ邮箱,《蓝莲花》的歌词被张小龙买断版权放在页首,已经很多年,企业家李宁曾经邀请他帮忙录制广告曲,王菲被发现去听他的演唱会,演员夏雨靠听许巍的音乐度过了低潮的日子。王朔复出后写的第一本小说《和我们的女儿谈话》里提到「许人家高」的《蓝莲花》,他写道:「《一无所有》以后多少年没再碰上一首歌,一下就把你心揪起来,顶到嗓子眼噎着你。」
最近直播平台上有一个视频的点击率很高,是许巍《曾经的你》多人演唱的合辑。视频的背景有时是有昂贵乐器的商品房,有时是在卡车停顿的路上,在油菜花农田,或者在更远处的大自然,树木的茎一束束地翻出地面。一个棕黑皮肤的男生抱着吉他,皱着眉头坐在山前,身后有晒在地上的苞谷、红色油漆的女士摩托车、没有贴上瓷砖的低矮民房。他唱着唱着,公鸡发出了打鸣的声音。里面有看起来很专业的音乐人,有满脸皱纹的老汉,不论平时听得更多的是摇滚传奇平克·弗洛伊德,还是网络歌手冷漠,大家都能唱一句:「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听众庞大复杂,但很少看到许巍被狂热追逐的报道,他的被偏爱好像都是安静的。一个喜欢摇滚的女生在网上购买唱片,对方问她平时听谁的歌,她说了许巍,得到了被赠送的另外几张CD。存在感不强,但又从来没有被忘记,许巍的音乐类似一种生活的背景音。
但作为最早站在流行和摇滚分界线上的那批人之一,他的音乐并非没有争议。许巍总是穿着普通短袖和牛仔裤站在台上,唱又「温暖」又「出世」的摇滚,没有强烈的愤怒感,这不符合人们对摇滚的已有认知。于是在很长时间里,他既是边缘人的「叛徒」,又是主流的「异类」,一直背负,却鲜有解释。

寻找
吉他手李延亮是在90年代中后期认识许巍的。「我去红星帮人录专辑,许巍当时就住在那儿,穿一大趿拉板,一秋裤,长头发扎着,刚睡醒,窝窝囊囊的,老躲在那外头,透过玻璃看我们排练。……第一次见面是这样的,反正那个阶段他都是那种特邋遢。跟他当时喜欢的音乐也有关,(涅槃乐队的)科特·柯本什么的也是邋里邋遢的,老穿一大秋裤就出来了。」
1995年,许巍来到北京,签约了陈健添的红星音乐生产社——他曾一手捧红过Beyond。第一次去公司的时候,许巍听到公司里放着自己最喜欢的涅槃。在当时的中国,摇滚是音乐里一个很小众的分支,而以涅槃为代表的「邋遢摇滚」听众更是不多。它是那种如果痛苦让人想要嘶吼却无法嘶吼的时候,能够在耳朵里帮忙释放的音乐。
从中学拿到吉他的那一瞬间开始,许巍已经为音乐漂泊了太久。摇滚席卷个性青年的时候,改革开放带来了以洋垃圾形式进入中国内地的「打口带」和港台资本,第一波的冲击催生了崔健这样的本土摇滚明星。他正当红的时候,许巍在西安的一次吉他比赛里拿到了第一名,他开始在各地走穴演出。选择梦想好像是选择了一种困窘,第一场演出他拿了一块钱,饿的时候一天吃一顿,但那年他18岁,不觉得怎么痛苦。「我们到一个地方演出就跑到剧场最高的地方写『天涯浪子』,还签上自己的名字。」后来的「西北鼓王」赵牧阳是当年和他一起的跑场走穴人,他在接受汪涵采访的时候回忆了那时候的生活。
一年之后,许巍回到西安,当了文艺兵,得到了被保送进军医大的机会,他可能成为一名牙医。但看完崔健的西安演唱会之后,他接下来的一月脑子里都是崔健,「那时候他是我的偶像,也不能拿偶像来说,就是一下打开我,(是那个)让我觉得『原来我要干这个,我想干这个』的人。」
他决定带着用全家的积蓄购买的电吉他去南方的歌厅里闯荡,赚回钱,成为西安最牛的吉他手。相比于音乐,歌厅的日子好像和涌动的金钱关系更大,有钱的人花重金买洋酒来摔,给歌手送花篮,最贵的500块一个,有人会送10个,「这边一听送了10个,那边就要送20个。」在歌厅演出是很多摇滚歌手都用过的维生手段,但不是他想要的。1992年,黑豹乐队推出了同名专辑,他又被推了一下,春节回家之后,他没有再出来,终于下定决心要自己写歌。
在西安,他和朋友组建了自己的乐队。许巍擅长写旋律,在当地很快有了一些名气,一度有人用摩托车的大灯照着找他要签名,乐队还受邀去参加了银川的「西北摇滚节」。但摇滚没有办法解决生活,乐队形式好像和他最初想要的还是有差别。回来之后乐队「悄悄解散」了,许巍是最后一个知道的。这个消失的乐队名字叫「飞」,是一个很自由的字,来来回回地轴转,他还没有飞起来。
他把希望放在了北京。和红星生产社的五年合约里,许巍推出《在别处》和《那一年》两张被摇滚青年青睐的专辑,是非常正宗的地下摇滚。早期的MV里,他留着一头及肩长发,穿黑色的皮夹克,镜头扫到的时候除了手在弹吉他,身体和表情几乎是静止的,感觉又颓又酷。
高晓松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许巍,他、窦唯和一帮北京朋友站在红星生产社后面的「旅游棚」听他录音。「他唱了一首叫《两天》,一首叫《执着》,那两首歌好听得我们当时所有人都惊了。」乐评人郝舫在90年代开了一家书店,兼卖唱片,在那里他认识了许巍,听完那两张专辑,他也很兴奋,「我认为在当时,没有任何其他人能玩成这样的。」
虽然得到了圈内人的认可,但许巍比以前更痛苦了。他住在一个不到8平方米的房子里,靠预支版税过日子,他当时的歌不适合KTV,也不被商演偏爱。而屋子外面的唱片行业来到盗版时代,按照媒体报道,当时大热的任贤齐《心太软》,正版和盗版的比例是1:10,只做唱片很难赚钱。
「《在别处》发行之后成就了三个乐手,包括我在内。一晚上,乐手不变,主唱变,都是许巍、张楚、高旗那种。一晚上我都在弹,挣四份钱,我们收入都比老许好。」李延亮告诉《人物》。
那时候独立音乐人都很穷,换着地方蹭饭,有一些人能安于窘迫,一个知名乐队的歌手,他把能够蹭饭的地方排上号,按照顺序去蹭,这样再见面的时候还能说句「好久不见」。许巍不是这样的性格,他逐渐把自己关闭起来。
郝舫被邀请去过很多歌手的住处,但没有去过许巍的,他不想开口,因为怕许巍不会拒绝,却自尊心受伤,他不想自己的亲近带来的是伤害而不是关心。
有一件事让郝舫记忆特别深刻,一次许巍到他的店里,看到几张美国最新乐队的专辑,问是什么风格。「我知道他想听,但是CD一张130块钱左右,比我当时一个月收入高,我就说,『你拿回去听,听完以后包装弄好,我再卖给别人就完了。』我也不只是对他一个人这样啊,但他来还唱片的时候,又给了我一张唱片,是张亚东的第一张专辑,上面应该还签着名。他说,『这是亚东的唱片,我觉得挺好的,你留着听吧。』」
那时候,许巍有很多的问题,但他几乎不向外表达。社会学家涂尔干给过「痛苦」一个描述,说这种感受来自于神经系统受到的过分强烈的震动,越是敏感的神经、越是强烈的震动,越是容易造成痛苦。两个条件,当时的许巍占全了,在录制第二张专辑结束后,他身无分文地回到了西安。
追逐别人的这条路,他执着地走了太久,但好像就是走不通了。这一年,他没有办法再像走穴时那样潇洒地写上「天涯浪子」了,他已经30岁,也有了家庭。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当时的心愿很小——「我每次见父母,想给他们买点礼物,每个月给钱养活他们。」
写给田震的另一首歌《自由自在》里面,填词人顺着他的曲写:「我没有选择,一片空白,我没有选择,坠落尘埃。」

受访者供图
奔跑
回到西安,许巍不太好意思见人,「传说我都挣了好几千万了,我都傻了听着。」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湖,他跑步,一开始跑三四圈就累得不行。有的时候他坐在街头看别人的生活。挺好的,哪怕开个小卖部也挺好的,至少能够理直气壮地活着。
他找到以前部队里认识、后来复员经商的一个朋友,说自己想要做生意。朋友拒绝了,他是见过许巍一天弹10小时琴的人,这让他印象太深刻了,许巍还是得做音乐。
后来在湖边能跑上更多圈的时候,他能重新捡起音乐,之前的音乐拯救不了他,但在甲壳虫乐队和U2这种以前被他认为太过流行的音乐里,许巍感受到了别的东西。他后来和郝舫聊过,「他那时候提到的一些人的音乐,我认为是属于那种有人的爱,也有一种大爱。比如说像约翰·列侬的《Imagine》,听起来是恨天恨地,谁都不服……但是他有一种真的是对人的那种爱,就是你谁都不相信,也要相信人类,相信自己,相信爱。」
在这之前,他热爱的涅槃乐队的灵魂人物柯本用一把能瞬间射出很多弹片的霰弹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离开的那天晚上,上万人的追悼会里,3个人选择开枪自杀。这件事情给许巍带来了震撼。「这让我开始思考音乐为什么会对人的影响这么大?我不太喜欢那样,至少我不希望听我的歌儿的人是这样的。」
这么多年里,许巍一直在往前走,走到穷途的时候,他不想成为摇滚明星了。「以前我想唱给能懂的人或者说小众的,我觉得年轻这样是没有错的,但现在我更愿意为所有普通人唱歌。一个工人回到家,当他觉得生活有很多不快乐的事情,如果听我的歌我能温暖到他,我就觉得特别高兴。」在回到北京之前,许巍已经逐渐地做了这个决定。
在他已经能围着湖跑十三、四圈的时候,朋友帮忙牵线找了百代公司下面的步升唱片(也就是后来的「金牌大风」)。许巍搬回北京,换了个地方跑步。在北海公园,他看到了很多以前被忽略的东西,比如外来的人、带着孩子的人、买菜的人、开小店的人,晚上公园里还有老年合唱团。「这些普通人,我就特想了解他们过得快不快乐、生存是不是很不容易。……他们可能没有那么时尚、没听过那么多时尚的电子乐、摇滚乐,可是他们跟你一样是一个人,有情感。我开始关注这个,这是我最大的一个转变。」
许巍不经常听自己的专辑,只有《那一年》这张专辑他偶尔翻出来听。它里面有浓缩的痛苦,让人不得不清醒过来。「你知道你是一个普通人了,从艰辛的状态为了生活挣扎奋斗,你没有那么顺利,你才能去关心周围最普通的人。」走过近乎崩溃的底点,他才切身明白什么才是他要做的音乐。几乎一无所有的他,抱着吉他在阳台上写了给父母的歌,里面他唱:「希望自己是你,生命中的礼物……」后来许巍的音乐里总有一种脆弱的力量感,它不愤怒,也一点都不激昂,最后一个字的唱腔总是向下滑,悲观的生活和旺盛的希望,他同时承认。
跑回到北京,许巍没有穿以前的皮夹克,过肩的长发也早就被剪掉了。但跑着跑着,离开了摇滚明星的梦之后,许巍出名了,很多首摇滚歌曲具备了流行歌曲的收听量,他成了流行歌手。有一次他回西安见到发小,她恭喜许巍终于得到了小时候想要的,但他反应很淡,「我一直在等,我都架好了一直在等,还总没等来,所以就放下了。哎呦,又来了的时候,没反应过来。」
这是许巍对公司的安排最配合的一段时间。明星这份工作不仅仅关乎创作,出一张专辑,公司会有传统的三个月宣传期,每天通告排满,从早上6点开始,最早的电台、电视台节目,再到晚上的歌友会,许巍都是懵的。他并没有拒绝,再痛苦都会坚持下来,身边的那些专业团队都很敬业,不是他能够说出口不要的时候。
逐渐在街头能被认出来,他离真实的生活越来越远。2005年他的第一场演唱会,许巍是坐地铁过去的。他喜欢选择公共交通,但有一次坐公交他被一帮初中生认出来,他们哄闹着让他唱歌,车上年纪大一些的人并没听过许巍,他就被架在那儿,为自己影响了别人的生活感到抱歉。这种状况遇到的次数多了,他不得不换了出行方式。
他不是那种常规的创作者,经历了后来《此时此刻》专辑制作的臧鸿飞说:「咱们大多数作者写作是方法论,方法论的人高产,但是他的作品都保持在一个相对不错但没办法到那种(直击人心的)感觉。有些人是相对低产,像许巍,他就没有什么方法。」如果非要说许巍的音乐有什么捷径,那只有他对生活足够重视,有时能够兜住普通人经历了却说不出口的感受,但成为一个流行歌手,越红便越注定无法拥有真实的生活。
他做不好这份工作,面对镜头太过紧绷,衣着不讲究,出租车司机都要给他提意见。当时公司安排许巍在湖南卫视上一档娱乐节目,晚上吃饭的时候导演直接对他说,你是真的不适合综艺。「人不适合,你就不喜欢,受不了,因为你说服不了自己了。」许巍说。
2002到2008年,许巍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最频繁的几年,他却过的是一种出世的生活,天天练八段锦,爬山、喝茶,读「圣贤书」……经纪人总找不到他,因为他不开手机,三五天看一次,看到了回一下。「当时公司所有的人管他叫老爷。同在一家公司旗下的陶喆只比他小一岁,外号却是公子。」
一开始是郝舫给许巍推荐了《Beat Generation》这本书,写美国「垮掉的一代」,这个文化分支影响了很多许巍喜欢的音乐人。他发现源头那些人竟然都研究过东方文化,转了一圈,他一头扎进了中国传统文化里。那时候许巍最喜欢王维的诗,类似的景色,杜甫写:「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李白写:「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但是王维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具备一种绝对出世的辽阔感。这些,也潜移默化地进入了他的音乐。
2008年之后,他开始拒绝外界几乎所有对他音乐之外的关注,他又跑掉了。「你对自己一定要诚实,对自己不诚实就完了,就真完蛋了。」
许巍做了《此时此刻》,这张专辑除了公司给的80万,他还自己掏了140万请了国内最优秀的一批音乐人来参与制作。封面是他们在云南一个自然保护区里露天演出,没有观众。
李延亮是封面小人头里面的一个,他回忆说:「当我们把一堆乐器放在大山里的时候,你自己是可以放空的,你融入到那个山水里,它让你真正回归真我。我们在山谷里录了三天,录音拿回来,发现很多大自然里的声音,特别美妙——嗷嗷两声鸟叫,小河潺潺的河水『哧』,一艘船的桨在旁边划,它们都很静静地在走着自己的路。」
这是许巍和郝舫说过的,人生最大的享受。一路跑到这里,他平静了。

自由
制作《无尽光芒》的这几年里,许巍发现自己能够发呆了,一直以来他总在不停地想一些事情,现在好像脑子允许自己放松了。身在城市里,他逐渐找到了一种不需要远行的自由。
他带着一种「安利」的语气向《人物》推荐电视剧《庆余年》里的一个片段,「有段男主人公喝多了,在朝堂上开始读《将进酒》,把我感动坏了。你看着自己的文明这么灿烂,那段太精彩了。」许巍不需要上山了,生活里本身就有。
「我今天来的时候还在想,我为什么永远都在调整自己心态呢,我说我调什么呀?我能活到现在多幸运啊,你说我从前郁闷的时候站在那儿就想跳下去,那一念之间,说没就没了。但是我现在还在这儿,我还有什么想的呀?」可那天早上刷牙的时候,他为前一晚弹琴到凌晨感到自责。「我怎么这么不自律,今天起来是有工作的,我怎么能这样呢?」这是很真实的许巍,总给人感觉像一团自己扭打在一起的线团。就连演唱会耳返出了问题,这种无法把控的因素,也会让他把矛头指向自己。
「以前有时候挺难受的。」站在舞台上,他一个人,不仅要承受面对上万人的压力,还要同时解决很多属于自己的「拧巴」。「今天灯光出点事,明天可能是别的,反正总有事把你激着。你在那个状态,突然一下拧巴了,哎哟,那是太难受了。那两股力量,下来以后,我一个人要调很长时间。」后来有次许巍和王菲有合作,就问她情绪不好的时候在台上怎么办,「就必须得唱完,唱完回去自己调,那怎么办?」大家都是一样的。
还是会自责,但从自责到原谅之间,没有了漫长的拉锯。结束拍摄,与《人物》聊天的时候,许巍状态已经调试得很好,他敞开坐着,没有把身体掖在板凳里。「我也不喜欢以前的我自己,太难相处了,真的。」他笑着说。
负责这次演唱会的导演王婷婷在2018年见到许巍。她是多年的粉丝,在还没有MP3的年代,她提着面包机,边走路边放许巍的首张专辑《在别处》。进入演唱会的筹备工作之前,她去上海见到本人,大家坐在一起谈论的是美食,「当时一起吃饭,有道菜叫糟卤鸡,特别好吃,吃完了我刚想说没了,许老师就说这个要不咱再来一份吧,我心里在那儿拍手。……之前也见过一些成名成事的音乐界的人,总是觉得特酷,有点凡人不理的那种状态,但是许老师他完全没有那种,是一个特别容易让人觉得亲切的人,挺活泼,挺好玩的,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郝舫是许巍快30年的朋友,「我亲眼看到他从比较自闭的那种状态变成一个更开放、包容的人,这件事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可能发生的……他以前就是很严重啊,这种变化远远超出想象。」
从许巍第二次回北京,郝舫发现他不再只当个好听众,能发出回音了。「有些事儿他要有礼貌地辩驳一两句了,他也不会直接反驳你,但是会举出一个别的例子。你就会觉得,哇,他比以前活泼了,老许其实是个挺可爱的人。」现在他们聊天,许巍的话多,有一次他们见面,吃饭完已经聊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住得起码相隔有十几公里,那天他就非要坐进车里,说我再送送你,再聊聊。聊到我们家门口,我跟他开玩笑,我就不送你回去了,然后他自己坐那个车又返回去了。」
许巍音乐团队中的笛萧演奏家陈悦对此也有明显的感受。2018年,许巍突然问她:「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演出?」陈悦当时在国家大剧院有一场专场演出,许巍主动说:「要不我给你助阵?」「结果许老师真的就带着团队去了,还专门背了设备参加了好几次的彩排,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也许是同样体会到了这样的变化,2018年鲁豫再次采访许巍的那集视频,用了鲍勃·迪伦一句经典的歌词:「我曾经老态龙钟,而今风华正茂。」

这种逆向,不似孩童式的轻松。
这几年里,他的身边有人离去。曾合作多年的「鼓三儿」张永光先生在2014年去世,「此时此刻」巡演邀请到的美国殿堂级鼓手约翰·布莱克威尔在2017年去世,这些都曾是他「蓝团」的成员。还有母亲,第一个给他买来吉他的人,前两年也因病离开了他。
「离别,多少的离别,一次次出现在我生命里。」《无尽光芒》的第一首歌《只有爱》的第二段歌词就以「离别」开始。而谈到《春海》这首写给母亲的歌,他说:「每次我想她的时候,我不想回忆那些难过的事,我只想回忆美好。庆幸的是这些年我每年会带他们去旅行,去云南、杭州、三亚……有一次我特别想她的时候,想到我们在三亚,我在沙滩上跑步,爸爸妈妈坐在那儿看着我,在阳光里。那一刻在我心里定格了。每次想到那一瞬间,我的眼泪都止不住,我想把它写成歌吧。」
前段时间许巍在西安演出,他回家了。那天的阳光很好,父亲坐在阳台上看书,许巍就坐在对面。等弟弟下班回来,三个在一起聊天,许巍突然感到了幸福。「其实聊什么真不重要,一家人在一块太重要了,一年能有多少次?太少了。以前我爸说一个什么,我在那儿哇啦哇啦,就挺傻的,现在不会跟我爸再争什么……我到50岁才懂得这些,太晚了。」
余下的自我挣扎不多了,譬如「孤独」。每天所有人都睡了,他一个人还在弹琴,持续地面对自己,半夜了,连说话的人都没有。从年轻时候开始,他今年要52岁了,「我一辈子都要这样吗?」但是弹着弹着,他发现音乐给他带来孤独的同时,也给了他新的东西。以前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古典音乐家能把巴赫弹一辈子,但现在他能体会了,「他每演奏一次,生命都会焕然一新一次,每拉一次,他的宇宙、世界观就会变一次。这才是真正做音乐的人……只要你做这件事,还有恭敬心,你就能感受到更多,只要在大道上往前走,一定就有风景。」
到今天,外界对许巍的争议还在继续,关于他的音乐「是否摇滚」「是否愤怒」仍在争辩。2012年郝舫邀请他去做了一次访谈,那次他回应:「前辈专门给我叮嘱,唱片下来以后,你可千万别聊摇滚,你就聊音乐就行,千万别被形式给束缚,不要给大家带来观念上很窄的东西,你要和大家说,我们在做音乐,我们还在学习,我们还想更扩展自己,去感知新的境界。」时间继续向前,争议还在原地,真实的许巍已经走到了更远的地方。
「不可能跟所有人去解释,让他们都能去理解你,太难了。过去你会觉得,比如做音乐,比如生活里,你做得很好了,但别人不理解你。其实你不需要别人理解,你只要知道你做的事情,是对的吗?喜欢吗?如果是对的,是喜欢的,那就往前走啊,那就不需要谁来承认你。那都是累赘,会给人带来更大的困扰,你只要向外求,你一定会痛苦。」
音乐也反射着他的变化——2012年他在《此时此刻》里写「无论欢乐和悲伤,我已不会再回头,只是自在向远方」,算是一种出离。但在2018年的《无尽光芒》里,成了「愿所有的创伤,能让我变得更勇敢」。
这未尝不是一种自由。

光芒
2019年末,许巍的巡演来到郑州,它是一场能瞬间把人拉入氛围的演唱会,靠近舞台的地方,鼓面的震动发出来的声音被音箱放大了无数倍,音场把人包裹起来。台上的许巍看起来还是那样,一根话筒,短发,穿短袖,长牛仔裤,放大的现场镜头里他的额头大颗大颗地渗出汗珠。
但演唱到某些歌曲的时候,观众的眼睛会有些忙碌。那个被他们目光一直追逐的人在舞台上跑来跑去,有的时候他会跑到吉他手李延亮身边,对弹一段solo,到尽兴处,他把自己的身体向后拉开。有的时候他会跑到舞台的最后面,鼓手杰夫在那里,他得边摇头边对对节奏。偌大一个舞台没有什么他没有「光顾」到的点,还能捕捉到他做一些鬼脸。
他的一个发小站在台下,这是她第一次因为听许巍的歌哭了,那首歌的名字叫《心中的歌谣》,是一首以前少出现的、很轻快的歌。一路所行,许巍几次沉进谷底,到此时他的线团能被自己扯开了。
近年许巍常常提到自己喜欢《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纪录片,里面的师傅在离开工作之后就过日子,类似他现在的状态,既认真又松弛。以一个音乐人,而不是流行歌手和摇滚明星的身份在生活里试图站稳脚跟,许巍在有的地方做了减法,在别的地方就得做加法——「好好把事情做好。」他常说这句话。
张彧发现在许巍的乐队里当一名键盘手有些不一样,在其它的乐队,张彧上台前会喝威士忌,不够燥不行,但演奏许巍的音乐,每个人都要非常精准地完成自己那部分,集中注意力,演出才能算演好。「我要保持非常高的清醒(度),红牛兑着咖啡哐哐灌上一罐的那种。(笑)」
新专辑是一张大家「认真玩儿」出来的专辑。创作还是那样,生发于许巍自己,有次他出去跑步,脑子里突然有了旋律,但手边没有记录的工具,又赶忙往回跑。六年里,他写了太多的音乐动机,放着,隔一段时间再去听,把能够在时间里靠岸的部分留下来,专辑定下来之前他删除了12G的录音文件。
但这次的编曲来自于全体乐队,大家来回碰,选择出最合适的版本留下来,然后在每一次的演出里复刻这样的合适。
如今每一场演出,不论是演唱会还是商演,许巍总是带着自己固定的乐队,有的时候他会带上一支20多人的队伍,都是国内国际最顶尖的一批音乐人和音响师。作为一个摇滚团队,许巍很重视鼓手,他从苏格兰请来了殿堂级的杰夫·达格摩,这个名字曾经和娄·里德,伊基·波普这些国际著名的摇滚歌手一起出现在巡演里。
一开始并不是这样,许巍刚接到商演的时候,国内现场演出的环境多是唱伴奏带的形式,就像唱卡拉OK一样,歌手,助理加上一名化妆师就是全部的成员。经历过那个年代演出的李延亮笑着说:「十年前,可能中国乐队现场都听不清主唱。」
许巍一直希望观众能得到真正的现场,但当时现实并不允许。他不擅长「抗争」,要求外界一定要符合自己的标准,也不擅长「妥协」,让自己符合外界,所以他选了一条辛苦的路。从2007年开始,他决定自己出钱带音响师,慢慢地变成自己带乐队。顶尖的音响设备只有北京有,许巍也自己出钱把设备从北京调到现场,他去哪里,就运到哪里。
他很后悔在过往的采访里聊到这件事情,他觉得当时自己的一些表达容易让人觉得他是一个「榜样」。「我觉得所有人能现在在一块儿,还是因为大家对音乐都一样的态度……不是因为许巍,跟许巍没关系,真的。」他不想成为「箭头」,而是梦想成为一种「介质」,像一束光里的粒子要属于光才有意义。
李延亮和《人物》聊许巍音乐的时候,也提到了光,他说:「我们是脆弱的,很不行的,但是你可以行,你怎么行?你要成为一个小量子,跟着银河的星星走,就会很顺畅。我们每个人都是光,你在这个世界上照亮你身边的人,照亮更多的人,照亮你能照亮的人。」
2012年,许巍去澳大利亚听了一场U2的演唱会,他站在人群里,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感动得落泪,再看旁边的一个白人男性,也哭了。像是一个圆环,许巍又回到了以前年轻的时候那种「追星」的状态。这是音乐的力量,在某个瞬间,人好像星星一样被更明亮的光给点亮了。
后来许巍在看话剧的时候,他发现所有观众的情绪能够被剧场带着走,像绳子一样拧在一起。于是让朋友帮忙推荐合适的话剧导演,试图把话剧的那种讲述感和场域感结合到《无尽光芒》的演唱会上。导演了《战马》中文版和《金沙》、《钢的琴》等音乐剧的王婷婷第一次以许巍的音乐为剧本去构思完整的舞台。她说,演唱会的每一束灯光都是她从别处借来的——「当时我在一个热带国家潜水,阳光让人觉得通透和丰富极了,早晨的阳光、傍晚的夕阳、以及你在水下看到的阳光,正午时候那种刺眼的阳光,在树林里走,透过树的缝隙出来的那些阳光,那个时候我觉得,哎呀,我找到了。」
舞台灯光暗的时候只剩下几小束射灯,它照着李延亮横放的吉他,他要用吉他弹出古琴的声音,蓝色的光,凉凉的,把人拉到绝对沉静的空间里去。而灿烂的时候,荧幕上放映着暖黄和橘红为主色调的专辑封面,前十排完全被燃烧的灯光打亮,许巍站在封面的那轮太阳前面,有的时候他不唱歌,他听。
全场大合唱的时候,镜头换着方向随机给观众特写。很多人的穿着都「不够摇滚」,甚至有些「太过普通」,但不分座位档次,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个造价不低,能够自动控制灯光的蓝莲花手环,从高处看去,一片光海。

受访者供图
有的人开始落泪。臧鸿飞曾经评价过许巍的第一场演唱会:「每个觉得自己相对悲观的人,可能都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人,但是有一天突然在一个可能一万人的场地,发现原来有这么多和我一样的人,那个场面就特别感人。那个全体大合唱的时候就和合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不一样,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我是一个特孤独的个体,我喜欢的歌可能没人喜欢什么的,原来有一天大家到了工体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
在乐评人的角度,郝舫觉得许巍一定是要被写进中国摇滚史的人,他对《人物》说:「评价艺术家,一种是评价他们的作品在细分领域里一直得以流传,成为经典,这是一种方向,这很了不起。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他能跳出之前的艺术领域和流派,赢得不同身份人的共同的传唱,这样我认为也了不起。」
他解释,音乐的流传度和「跨界流传度」,「不能简单说一首歌传唱得越广,它就越了不起,不能这样判断,得看它是仅仅被普通的音乐爱好者喜欢,还是为这种音乐赢得了更多的听众。如果本该是一种被限制在小众范围内的东西,却有人为它赢得了更多的听众,我觉得它不是一件坏事。」有一次去新疆,郝舫听到了司机在放许巍。
对于现在的许巍来说,并不是为了成为什么而做音乐的,明星、榜样,在他心里都没那么重要了。郑州演唱会那天,有年轻的男生在台下喊「牛x」,声音很大,许巍在心里惭愧。他总觉得自己德不配位,只把自己当成演唱会的领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们都是被音乐拯救的人,我们都在一块,只是位置不同而已。」
坚固的更加坚固,消失的已经逐渐消失,一些细微的变化就像「冷笑话」一样被夹杂在与许巍的对话里,被夹在当天听众迅速而整齐的退场里,被夹在许巍乐迷群里的一条「明天过节,大家留个联系方式,我给你发祝福」的状态里。在许巍的豆瓣小组,没有什么聊许巍这个人的帖子,大家互相挪票,听歌,在小组的首页看一句:「谢谢你,老许。」他继续像我们周围的空气一样存在着。
「有一次演唱会期间,我在街上走,也没有人认出我。我突然问别人说,我是不是过气了?怎么没一个人认识我?」许巍笑着,「他们就乐,我老逗他们,但是其实票房一下就秒光了。我觉得挺好的,没有人认出来太好了,太自在了,你根本不用过脑子。时间长了,你是放松的,你在街上走,你也不觉得自己是谁,你看到的东西是一种很生活的东西。」
北京傍晚的天色暗了,许巍的肩膀逐渐松弛下来,冬季的空气冰凉,他钻进自己的车,当天的工作结束,他立刻离开「明星」这个身份,要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