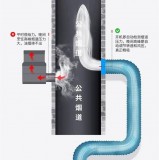应了一首老歌,时光飞逝如电,倏忽间又是一年。八十多岁的老父老母依然热衷过年,提早一个月便筹划回六安老家,并选择小年前一天返乡,儿孙们当然只能紧随其后。
三十年来,随着二代人进城务工、就业,村里几乎只剩下为数不多的老人家,田地交给种田大户经营。过年,村里再无猪可杀,鸡鱼肉蛋超市里应有尽有;随着洗衣机的普及,各家再不用在寒冷的天气里捣开冰冻洗衣服。许多现代化的便捷之后,魂牵梦萦的年味也变了。
小时候的年味,从腊月开始。腊月二十左右拐汤圆(磨年糕),将糯米洗净,在清水里泡个一两天,用最原始的方法——人工推磨将泡松软的糯米碾碎后晒干。大年三十、初一早上,糖汤圆或菜汤圆是餐桌的主角,一锅里有一两个“元宝汤圆”(包有二分或五分的硬币的汤圆),记忆犹新多个大人孩子中奖元宝汤圆的笑脸。
小年前开始大扫除。拆洗被褥是个大工程,选择好天气是关键。其次,用热水浸泡被头上一冬攒下的油渍,接着用洗衣粉搓洗后,到结冰的塘里清洗,用棒槌捶,甚至穿上雨鞋踩,再用手拧干,一两天便能晒干。多年来,记忆里仍有肌肤接触干净被褥的舒服及被絮里所含的阳光味道。
二十七八杀年猪。儿时胆小,既怕杀年猪,也盼杀年猪。烫去毛的猪被开膛破肚,劈成两半,一半卖掉,另一半给主要亲戚送点,自己家里所剩无几。好在杀猪当天,基本能敞开肚子吃顿肉,然后把余下的束之高阁,大年三十、正月待客用。
年夜饭的筹备是全家总动员,杀只鸡、酥条鱼、贴对联,各尽其职。开年夜饭前,先烧香祭祖。祭拜结束,燃放鞭炮。挨到年夜饭开席,孩子们狼吞虎咽扒点能动的饭菜(咸肉类的菜一般是摆样子留到正月待客的),便急吼吼赶去长辈家辞岁,以便收点压岁钱和花生糖果。殷实点的亲戚会准备好崭新的钱币,从五分、一角、两角到五角。现在的孩子不会理解,60后、70后的孩子曾为几毛钱的压岁钱,盼上一年的心情。
六安乡土人情浓郁,有句歇后语,“不怕家里忙,拜年拜到麦子黄”。现如今,生活变得殷实、富足、便利,亲朋邻里却日渐疏离,缺少动力的走亲戚拜年,反倒成了负担。一年到头难得见上一面,相顾却无言,共同的话题不多。混得不好的,羞于开口,混得好的,也想藏着,各家关起门自得其乐。父母健在,子女还返乡过年;父母过世后,没了念想,很多人清明时祭祖才回乡。故乡成了异乡。
相比往年,这个春节最平淡,可也最自在,既善待了自己,也善待了家人。三代人汇聚在爸妈曾经创业的房子,白天去户外徒步,晚上围炉夜话,老的少的畅所欲言,谈理想,话人生。一日三餐不是虚头巴脑的十个碟子八个碗,而是奉行极简原则,一道主菜、几个小菜,餐餐小酌,没人劝酒、拼酒,喝得舒服尽兴。
如今,90后、00后说着普通话,吃着汉堡,喝着奶茶,在互联网里找寻快乐;而我们这些60后、70后的童真、童趣,很多来自过年的穷快乐,是一代人半生的支撑和回味。当下不缺吃喝,也就对过年少了期待,随之消失的就是各种筹备过年的仪式。但新型的春节,自有理性、踏实的简单、健康和幸福。随着城乡差别的日渐缩小,以后逢年过节,或许更多在城里工作的乡村人会选择度假村,一家人集体过传统的佳节吧。(李元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