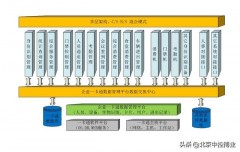澎湃新闻实习生 彭思宇
旅舍的位置并不难找。可我走错了路,跟着百度地图在隔壁大楼里绕了好几圈,最后还是抓住一个外卖小哥问了问,才看到派出所旁边“夜宿晓行”的招牌。只见几个男孩坐在楼道外,借着招牌的白光,一边抽烟一边侃大山。

2021年4月,深夜在旅馆门口抽烟的住客。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周平浪 图
这里就是传说中50块钱能住一晚的地方。来到上海找工作的人,从上海站出来,过人行横道,再过天桥,沿恒丰路走二十分钟,就能到这儿住下;早上出门面试,不必起太早,不到百米就是汉中路地铁站。
我爬上二楼,迎面是放满了外卖的架子,散发辛辣油腻的气息。旅舍的玻璃门需要刷房卡才能开。听到我说要办理入住。前台的小姐姐过来开门。除了被来往的人反复打量之外,一切都还顺利。我抱着前台给我的三件套——被子、枕头和床单,顺着混杂着人声、水声、手机声的走廊,找到了自己住的房间。
我要和这些来往的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了。

刚入住的年轻人。
一、羞耻
刷房卡才能进门。我所住的是个六人间。与走廊的明亮相反,门里是暗的。我借着门外的光往里看,三个下铺都挂着床帘,是有人住的。
我把被子放在靠近门口的上铺。又打开了灯。隔壁下铺一阵响动,一个女孩从床帘后钻出来,与我四目相对。我来不及打招呼,她又钻了回去。我顿时不知是否该把灯关上。我又开始收拾行李,只听到断断续续传来连麦的声音,她开始打游戏了。
我踩在上下铺之间的梯子上整理床铺。门又开了,进来一个四十几岁的阿姨。只见她略微挣扎地看着我脚上的鞋子,随即态度和善地问能否脱掉,不然鞋底灰尘会落到她的床上。原来她是我的下铺。我尴尬地立刻脱掉鞋子。阿姨冲我笑了笑,不知怎么牙都不全了。
她自称在这住了三个多月,也是刚搬到这间房。说起原因,她倒扭捏起来:“我不是那种说别人坏话的人。我们屋里那个小姑娘,一直嘟嘟囔囔。我年纪大点,说了她几次,她就骂起人来了。骂得难听呀。我问她,你骂的谁?她直接呛回来,骂的就是你。我可害怕了。昨晚在18号房凑合了一晚上,今天搬到这个房间来了。”
恰在这时,前台带了两个20岁出头的女孩来看房。她们大概是阿姨的前舍友,说昨晚吓得没睡着觉,要换房间。
从这些不同年龄、职业、经历的女性身上,我竟感到一种大学宿舍的人文气息。一阵喧闹后,人们钻进自己的床帘。
我拿出一包糖,问大家吃不吃。她们都拒绝了我,甚至床帘都没拉开,只说一句“不用,谢谢”。我又觉得,这个房间里的人,空间距离无比接近,但心理距离无比遥远。

一间客房。
我去楼下便利店买了晚饭,拿到旅舍的公共区域。要是在房间吃饭,气味难以散去。大家都在公共区域的桌上吃饭。位置有限,我在两个人中间找到空位坐下。像一家人那样,我们紧挨着,却只是自顾自地吃,丝毫没有交流。一旁还有人在剪指甲。一边是吧唧吧唧地吃,一边是咔嚓咔嚓地剪。落到地面的指甲屑,和桌上的外卖食物残渣一起,等着清洁工师傅打扫。
我胃口全无,随便扒拉两口,又回到房间。

洗漱间。
我所在房间门口是洗漱间。12个洗漱台挨在一起,男女混用。我第一次跟这么多陌生男女一同洗漱,身边有个大哥正在刷牙。人们不关心他人,抬头遇上别人的目光,视线也会立刻转开。洗漱台背面就是浴室,女生浴室与男生浴室连在一起。晚上九点多是高峰期,排队等了两个人才轮到我。浴室只有3个很小的隔间。我拿着换洗衣物进去,发现无处可放,一开花洒必然淋湿。但总不能光着身体从浴室走到房间,毕竟一出隔间,就是一排公共洗漱台。必须穿着衣服进去洗澡,洗完换好干净衣服出来。怪不得,之前在走廊上,见到只围着一条浴巾、近似赤身裸体的男人,而旁人却对此视若无物。

作为消防通道的楼梯是住客唯一能晒衣服的地方。衣物密不透风,不但不易干,挂取也不容易。夜里需要用手机打光仔细翻查,倘若取错再挂回去,又要大费周章。
我并没有浴巾可用,也很不愿这么做。我想到的办法是,把干净衣服挂到门上,盖上浴巾,再盖上换下的脏衣服,并用身体尽量挡住水花。洗澡竟是一件“提心吊胆”的事。浴室的隔间上下透风,门外传来陌生异性洗漱的声音。我完全无法放松下来,享受沐浴的乐趣。
在这些日常的吃喝拉撒中,我们这些住客紧紧挨在一起,但也终究不过是短暂停泊。对面的人随时可能悄然消失。因此,冷漠是一种默契,甚至是一种尊重,呆在床帘里做自己的事,才是最舒服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在公共区域的行为,也不必怎么讲究;在自己的房间里,需要忍耐的已经太多了。

独自在楼梯上抽烟的住客,身旁是手写的告示:禁止在此抽烟。
二、忍耐
房里充斥着人的气味,像挤满学生的教室。六人共有的一扇小窗,被东西挡着,只能打开一条缝。看来,通风和采光都难以指望。而我身下的床垫也不干净,残留着头发、污渍,自上一个使用者搬走之后,大概是没有清洗过。
洗漱间两端是公共男女卫生间,每间只有两个厕位。相较于几百个床位,数量似乎不太够。早晚如厕要排队。卫生和味道着实堪忧。
在洗漱台刷牙洗脸时,我想顺手洗袜子,发现洗手台上贴着:“禁止用热水洗衣,违者罚款”。我只好用凉水洗了袜子。
洗大件衣物可以去洗衣房。洗衣房和茶水间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洗衣机、一个烘干机和一个可以接热水的饮水机。三台机器占了大部分空间,剩下的地方仅够一人站立。我想用洗衣机,但有人把装衣服的盆放在一边,似乎在排队。我也把衣服放在那里,算作占位子。
我想知道更多住客的情况。借着去公共区域吃东西,我与旁边的男孩攀谈起来。他叫李昭旭,还在读研三,是金融专业,来上海想找公司实习并落户。

李昭旭
“怎么会住到这里来。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落魄。”李昭旭对我回忆起头几天的心情。因实习收入甚少,父母给他每月四千块贴补生活。但在上海市中心,这笔钱只勉强能租个单间。若租住在便宜的偏僻之地,四处面试交通不便。最后来到这里落脚。他忙于自己的面试和实习,和陌生人共享一间房,却完全不想融入“集体”,甚至一度深感忧郁。
我想看看男生寝室的样子。于是,在李昭旭的房间里,我见到了打扮入时的鞠家天。

鞠家天
父母在给鞠家天取名时,或许对他寄予了家如天大的希望。然而与名字相反,他现在的家只有一张床大小。
一年前来到上海,鞠家天落脚于此,就没挪过窝。期间还经历了旅舍装修和家具轮换。他笑称,自己比这些床铺的资历还老。我夸赞鞠家天帽子好看,他很开心地说谢谢。他买了香薰放在床上,床头还有一株百合花。
我意识到,在这样逼仄的环境里,一般人很难有照顾好自己之外的动力,而眼前这个男孩仍用力地爱着生活。
“宿舍一直有臭味,洗衣机老是坏,晒衣服的地方太窄,烘干机太贵,公区老是有人吃了饭不收拾……”对鞠家天来说,这个旅舍处处不合心意,但又似乎处处可以忍下去。

作为消防通道的楼梯,是住客唯一能晒衣服的地方。天花板上无时不挂满衣服,密不透风。不但不容易干,挂取也不容易。
也许心理上的艰难更为要紧。住在青年旅舍,似乎是羞耻的事,是需要小心隐藏的秘密。同事问他住在哪里,鞠家天总会搪塞过去。
并不是不想离开,只是成本难以承担。“找房子是问题,押一付三的机制是问题,通勤也是问题。”
即便如此,他还是想留在上海,因为大城市更为宽容,生活更为自由。
深夜来得很快,看房间的两个女孩没搬过来。今晚房间里有四个人。大家作息不同,下铺阿姨很快睡了,传来沉重且均匀的呼吸声。那个女孩还在玩游戏。我听到她与队友对话,她已有十五连胜。另一个女孩泡完脚后也在床帘里,不知在干什么。
12点钟,下铺阿姨的呼噜声有节奏地高昂起来。玩游戏的女孩还开着灯。窗外车流声和床下呼噜声交错。我实在睡不着。只听女孩起来,收拾了些东西出门,但把门虚掩着。我清楚听到洗澡的水声、洗衣机滚动的声音,接着是吹头发的声音。
呼噜和车流声已令我恼火,加上门外这些音效,实在应对不来。
我想下床关门,但看到床位的光,知道她没带房卡——卡片插在床头取电处,灯才会亮。她回来开不了门,就会影响所有人。手机显示,已是凌晨2点40分。我只好闭上眼翻了个身,各种声音刺激着神经,只觉身心疲惫,却无法休息。
半梦半醒中,拖鞋声渐响,那个女孩回来了。门咚一声关上,脚步声、水流声和洗衣机声隔在外面。我顿时感觉,只有呼噜声和车流声交汇,其实也已经不错了。
剩下的夜,我是熬过来的。闭上眼是睡,睁开眼是醒。床下呼噜一声比一声高,窗外车流声越发密集。早上7点,我爬起来,穿好衣服出去。门口是一排洗漱的人,男生居多。我一点也不想洗脸,此刻唯一的需求是静一静。
我这时有些明白了,为何旅舍旁边就是派出所。在这里,很容易遇到无法忍耐的事情,万一矛盾升级,处理起来也是极为方便的吧。

夜宿晓行和派出所毗邻,这让许多住户有安全感。
三、家宅
晒衣区在走廊尽头,连接着三楼的楼梯间。许多衣服挤在一起阴干。我向一个大哥借晾衣杆,发现他也是山东老乡,住在三楼的公寓里。

三楼公寓一角,垃圾桶和晾衣服区域。
他叫邵尚磊。住的房间有一室一卫,九个平方,一米五的床占了大部分空间。窗户面向走廊,没有阳光。衣柜、桌子和冰箱摆在床的一侧。中间留出一条通向水槽的过道。料理台在水槽边,一口锅正咕嘟咕嘟煮着面条。卫生间里只有马桶和花洒。

邵尚磊堂弟房内灶台。
邵尚磊和李文涛一起住。两个大男人要睡一张床。但月租只有两千出头,人均比楼下的青年旅舍还便宜。他到上海的第一站,是在叔叔和堂弟那里——先一步来打工的亲友,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给了他很大助力。后来,堂弟妻子也从老家来到上海。邵尚磊就搬了出来,与李文涛合租。

邵尚磊堂弟。
家庭还是第一位的,邵尚磊也有个五岁的女儿。“生活上过得去就行,能多攒点就多攒点。以后小孩上学了,要花钱的地方多得是。”如今在上海当快递员,月收入能达到近万,相比在老家的四五千块,无疑是翻了个倍。“孩子大了,肯定要以孩子为主。到时候,我回家找个工作。”他反复说,现在只想踏踏实实赚点钱。
不过,在他看来,当下必要开销也不少。“上海这儿,吃个饭就好几百块了。在外面吃饭,倒不是说多好吃,但朋友得处。人活着必须得有交际,得有朋友啊。一旦出什么事,起码有朋友能帮帮你。谁也不认识的话,啥也不好办。”

邵尚磊房间摆着女儿的照片。
豆角焖面出锅了。邵尚磊端着碗倚着冰箱,说起送快递的见闻。他说,外企里干活的,绝大部分是上海本地人。工资不高,五六千块钱,公司给交着社保,但啥都不愁,有个活干就行。

邵尚磊堂弟也在同一家快递公司,手上是为了找工作而洗去纹身后的疤痕。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背井离乡到这里来。要是一个月只挣五六千,早就饿死了。”邵尚磊言辞之间难掩羡慕:“人家的起跑线高,有房子不需要攒钱。而且,好多人都很宅,不出去也花不了多少钱。”
李文涛打趣他,让他当宅男省钱。邵尚磊只回答:“我不想当宅男,我想当上海人。”

李文涛(前)和邵尚磊。
而李昭旭在青年旅舍住久了,棱角似乎也被磨平。他说,自己内心已趋于平静。因为他已找到了实习的工作,被选择、被认可的力量,让他相信自己有搬离这里的能力。
鞠家天目前最大的愿望,是在工作单位30分钟车程内,租下一个单间。这需要他月收入达到6000块。以此为目标,他还在努力。

邵尚磊堂弟房间摆放着在老家拍摄的夫妻合照,他不奢望在上海买房,只想着打工尽力攒些钱。
邵尚磊依靠亲友落脚上海;以后有一天,他也许会意识到,最终真正能指望的还是自己。说到底,这就和楼下青年旅舍的住客一样。而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天地间的过客罢了。

夜宿晓行位于苏州河畔,两岸密集建筑体内开设着许多类似的旅馆,是许多人刚到上海时的落脚之处。
那么,何处是家呢。我意识到,在只拥有一张床的生活中,住客们被紧张、焦虑、担忧的情绪所包围。而他们自身也成为城市格局的一部分。也许,来了就为了更好地离开。或进或退,或悲或喜,都是这座城市宏大叙事中的一环。

张小姐和男友刚从河南新乡来到上海,到夜宿晓行发现已客满无房。他们原先在老家县城开美甲店,因为竞争激烈,来上海报班进修美甲,想要跟紧潮流。
责任编辑:周平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