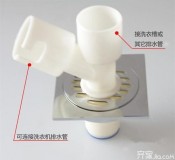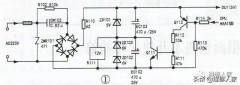2021年10月29日,《乌海》上映,
黄轩、杨子姗主演。
被影迷认为是年度
最生猛、最敢拍、最有劲的现实主义电影。
这是导演周子陽“道德困境三部曲”的第二部,
写剧本时,他身边有6对朋友相继离婚,
电影中很多细节,便来源于此,
直面所有人无法回避的问题:
金钱、暴力和性。

有人说周子陽的电影,
特别容易出影帝级的表演,
2017年的处女作《老兽》,
让老戏骨涂们拿到了金马影帝。
这一部《乌海》,
是近一年来获奖最多的华语电影之一,
相继入围西班牙圣塞,
香港、金鸡和海南电影节……
黄轩贡献出近年来最炸裂的演技,
拿下香港电影节最佳男主角。

黄轩饰演的男主角,
深陷债务危机,
婚姻关系也在破裂的边缘,
在三天内,
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史航说:
《乌海》是倒霉蛋的故事,
唤醒每个中年男人沉睡的内心。
有人说:
电影里的荒诞就是现实的提炼,
看得人冷汗横生。
从压抑到最后的爆发,
像抽了生活一耳光。


《乌海》原本6月上映,
随后突然撤档,终于在近日公映。
周子陽一度处于焦灼的状态,
一条在6月和10月两次前往北京,
和他聊了聊。
撰文 洪冰蟾 责编 倪楚娇



2019年底,《乌海》在内蒙古乌海市开机。
故事里的杨华(黄轩饰)和苗唯(杨子姗饰),曾经是一对相爱的夫妻。杨华原本有稳定的工作,结婚后,为了挣更多的钱,他就从企业辞职,去做生意,但欠了一屁股债,还偷偷抵押了妻子的房子,苗唯因此非常愤怒。
而另一边,苗唯在几个月前偶遇了大学时期的恋人,前男友想要和她旧情复燃。通过行车记录仪上的录音,杨华知道了这事,两个人的矛盾一触即发。

困兽犹斗
《乌海》的大背景,是早些年的鄂尔多斯。当地的人均GDP一度超越北京和上海,到处是房地产建设和拆迁户,都市财富神话层出不穷。
一些上班族,拿房子、车子抵押贷款,再用贷款去放贷。但随着2012年煤价下跌,手里的钱缩水,借出去的钱再也收不回来,一夜之间,很多人背上债务。

周子陽今年38岁,是鄂尔多斯人。他塑造的男主角,正是这个社会背景下的小人物,男主角的遭遇,很多曾真实地发生在周子陽身上。
他讲话带着浓重的鄂普口音,看起来是个西北糙汉,但说到动情处,会忍不住流泪。

为了拍电影,他蛰伏近十年。
他不是科班出身,毕业后两三年无所事事,在鄂尔多斯混日子。2009年,他到北京找工作,不停地搬家,天通苑、牡丹园,甚至住过厨房改造的单间,屋子里安着燃气炉,旁边有人洗澡,尾气就可能让他窒息。
逼仄的合租房困不住他的野心。他计划28岁前,拍出人生第一部电影,于是毅然决然辞了职,当时兜里只剩下6000块钱,他想去这个世界上最高的地方想剧本。从西藏回来以后,兜里只剩下2000块了。
好不容易写完剧本,却找不到投资。有一天,他去找当时的女朋友,从天通苑坐地铁到东直门,再走过去,就迟到了。女朋友问周子陽怎么回事,他说:“兜里就剩两块钱了,我一会儿还得坐地铁回去呢。”

尽管如此,他还是没能如愿在28岁当成导演。直到2017年,34岁,他才拍出《老兽》。《老兽》在台湾电影金马奖横空出世,4提3中,周子陽获得最佳原创剧本奖。
领奖的时候,他哽咽地说:“十年时间过去,这里面有焦虑,有疼痛,也有忧郁,甚至还有黑暗…...”
当时,他在经历人生的至暗时刻。《老兽》前途未卜,好朋友胡波突然离世,他们是同一年去的FIRST创投,周子陽带着《老兽》,胡波带着《大象席地而坐》,他们都寂寂无名,都怀揣电影梦,前后脚拍出了自己的作品。好朋友的离世对他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紧接着《老兽》上映,只有200万票房,排片不到0.1%。有人嘲讽他:“赢了面子,输了里子。”

因为金马的肯定,很快就有一个五六千万投资的商业电影来找他,但他拒绝了。
“其实就算接了,大不了耽误一两年,但拍一个不喜欢的电影,我觉得我就完蛋了,都坚持那么多年了,我要拍自己的东西,一刻都不能懈怠。”
他当时只有一个强烈的感受,生命随时会消失,必须做最紧急的事,就是电影。
2018年,他已经结婚5、6年,有两个孩子。没有收入,去借了二三十个网络贷,他不停地写,睡着了都在想剧本。除了写作,他还需要绞尽脑汁还贷款,每两三天还一次。
《乌海》就是在这样一个残酷的生命状态下创作的。

周子陽经历的压抑、绝望,原原本本嵌入在黄轩的角色性格里。
一开始就身陷囹圄,追债的人把杨华堵家里头,他大气不敢出。他开着车在不同的地点之间移动,越陷越深。世界这么大,好像亲人、朋友、家人都在,但是没有他的容身之处,被逼到无路可去。
《乌海》里有一段短视频,是人们从泥坑里,挖出一条又一条的非洲肺鱼。旱季的时候,非洲肺鱼会钻进泥里,泥慢慢干了,它会吐唾沫把自己裹住,直到下一个雨季来临。
“它困在泥里,最长能活5年,挣扎,甚至可以变异,生命的力量多么强大。”
以下是周子陽的自述:

真实的婚姻细节
2016年深秋的一个夜晚,我做了一个噩梦。
一个坏人,往我的腹部开枪,子弹慢慢地往心脏走。我在梦里想,我不能死,我还有我的妻子和孩子。我就一点点地挣扎,子弹钻进心脏,眼泪流个不停。惊醒之后,我坐在床上,那种疼痛感挥之不去,我想他们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后来,我听说了一个新闻。一对和睦的夫妻,两个都不是坏人,但他们陷入经济危机,一个就想把另一个给弄死。
从这个突发事件出发,断断续续一年多,我写出了《乌海》。

写剧本的时候,不知怎么,身边竟然有6对朋友离婚。《乌海》里的很多细节,就来自我身边的故事。
我和一朋友去看电影,散场后他站在马路牙子上,点了一根烟说:“我今天离婚了。”
有一天,他在家里的行车记录仪上,听到老婆在跟别人打电话,那个美好的声音和笑,他几年没听见过了。

《乌海》里,杨华因为听到行车记录仪里的对话,质问苗唯是不是出轨,怀的孩子是谁的,两个人都在怒吼,发狂,砸东西。我想结婚久了,外面看上去云淡风轻,关起门来,多数人都会争吵。
这一场争吵戏,我和黄轩、杨子姗关在屋子里,从下午聊到天黑。喊cut后,一时间他们都走不出角色的情绪。我想,这就是现实的力量,种种不堪和变故会震碎情感,让人久久无法走出来。


我也设置了一段美好的回忆,杨华在山顶跟苗唯求婚。那一场戏是黄轩和杨子姗手持自拍的,360度,就不能站其他人,会穿帮。
当时我把自己的手机交给黄轩,整个剧组就把他俩扔山顶,全撤到几百米外的屋子里。告诉他们大概的调度,具体的演法和拍法,他俩自由发挥。
我们都没法看画面,拍完一条,得把手机从他们那里送到我手里,看当时发生了什么。拍了5条,每一条都不一样。
黄轩原本要拒绝我的邀请,他之前出演了同样有巨大情感纠葛的角色。我就给他写长信,和他长谈,没想到他立刻答应了。
来剧组后,他主动提出要选一个光线差的房间,让自己一直处在压抑的状态里。他在兰州出生,本来就熟悉西北方言,为了电影特地学了乌海话。我们俩到现在,都是用乌海话给对方发微信语音。


涂们老师是我第一部电影《老兽》的男主角,当时我把《老兽》的剧本给他看,他以前根本不认识我。聊了两三个小时,他就接下角色,他说:“就像蚂蚁的触角一样,一碰就知道。”
这一次,我问他要不要来客串黄轩的老丈人。我们的关系很亲密,会去路边摊喝啤酒吃烤串,无话不谈,涂们老师喜欢说:“我们一起聊聊别人的坏话。”
我还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小角色,杨子姗给旧情人打电话,那个男人就是我。银幕初体验,不仅没露上脸,还演了个婚姻破坏者。

魔幻恐龙乐园
内蒙古的乌海,离我老家鄂尔多斯很近。那个地方,山、湖、沙漠交织在一起。我很喜欢这个名字,感觉有一种深邃、无边无际、隐秘感的东西,像人心,像欲望。
受到李沧东的《密阳》的启发,我觉得“乌海”像电影的主题。

最冷的时候零下十几度,七八级大风。内蒙的山到了冬天,就光秃秃的,没有植被就看不出风有多大。
真实情况是,一开始大家穿羽绒衣,羽绒衣哪顶得住,于是就抢军大衣,抢到一个算一个,摄影师手僵得都握不住机器。
我总拍冬天的戏,上一部《老兽》也是。我觉得人在寒冷之下,没那么温柔,比较激烈。

杨华,特别普通的名字,好像每个人身边都有类似的人。
他投了一大笔钱建“恐龙乐园”,但乐园黄了,投资款被好朋友罗宇拿去建沙漠里的帐篷“沙漠月亮”。不仅钱拿不回来,还把家里的财产抵押了。
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个老赖,是个不完美的角色。黄轩演的时候,全程脸上都带着伤,这个角色老是被打。被朋友打,被小姑娘打,甚至被路人打。这是我对人物的设计,他打架老吃亏。
我觉得打架厉害的人,就是解气,炫耀一下,很没意思。但是打架吃亏的人,心理活动就丰富,总想着怎么办,如何收场。其实这更像多数情况下的人,憋屈、窝囊、焦灼。

有时候,不是打不过,是内心受到了伤害。
我认识一个鄂尔多斯的男人,他带我去吃饭,跟我说今天咱必须花掉十万块。他有个朋友,没那么有钱,后来他们发生了争执,他就扇了朋友一耳光,朋友没有还手。
他们俩彼此有感情,但被打的那一个,个体尊严被极大地碾压,我就想要呈现,人如何去消化这种复杂的处境?
人性深处,最幽微最深的地方,可能是暴烈的。被逼上绝路,杨华对身边的人做出一件件失去理智的事,越努力挣脱,陷得越深,几乎毁掉家人的生活。
另一方面,他的所作所为,又都是为了挽回家庭。在看起来坏的事和好的内心之间,有一种对抗,人性深处,好像也是良善的。

电影,电影,电影
我以前的性格和现在相比,完全180度反转。
以前是幽默搞笑的,学校文艺汇演得压轴说相声。但是20 岁高考时,我不小心把手机带进考场,成为建校史上考零分第一人。
到了冬天,我最好的朋友意外出车祸去世。遭遇这些接二连三的事件,我像完全换了一个人,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跟人交流。
我老在想,为什么生命就没了呢?复读的时候,我每天只睡三个小时,疯狂地学习,白天上文化课,晚上学画画。半夜醒来,画室友睡着的样子。
上大学也这样,凌晨四五点,我学习结束,到阳台上一看,校园一片漆黑,才觉得今天没有白过。

杨华造恐龙乐园,罗宇建沙漠月亮,电影里的人物做了什么,现实里我就做了什么。
我26岁的时候,鄂尔多斯经济特别繁忙,好多人一夜暴富。我也想在一两年内赚够一两百万,去国外读书。
我问家里借了5万块钱,策划了一堆虚空的项目,挂在树上的蒙古包,把鄂尔多斯的富豪,弄到拉斯维加斯,在飞机上给他们做酸菜。
但我一分钱没赚着。朋友们打麻将,我就端茶递水,在旁边看电影。有一天下午我醒来,楼下的人走来走去,老头打哈欠,小孩蹦蹦跳跳,我一下子就流了眼泪,我不喜欢这样的日子,不能再浑浑噩噩待下去了。于是我就写简历,到北京上班。

写《乌海》的时候,睡得特别少,每天写15、16个小时。
身上哪都疼,感觉只有手指和脑子能动弹,在超高速运转,瞬间调整台词,在上下场之间切换。写完最后一场,脑子里“啪”一下爆炸,太高兴了,就感觉此前经历的疼痛和压力,什么都值得。这是创作带来的幸福。

我觉得我和别人不一样,当面对一个忽然来的利益诱惑,但它又不符合你的人生规划时,好多人会去做,因为觉得人生漫长。
但从20岁开始,几个朋友相继离去,我就知道生命非常脆弱,可能某个时刻就消失了,所以一定要做最紧急和最重要的事情。每次深陷其他的事情,我好像选择的,都是电影。
而这部电影,就是关于变化的时刻。我们中国人老话叫“世事无常”,无常的状况下,人产生清醒的意识,我们也看到这个时代里真实的欲望、道德、情感,然后更包容和关心当下的生活,珍惜身边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