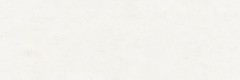文章较长,建议先马后看
在艺术与大众的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透视”早已不是陌生的词汇。然而说到透视的起源,更是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艺术家们最先摆脱开古埃及画家平面式的绘画方式,率先在作画中应用了透视短缩的方法表现人体,这是艺术史上的一大革新。

然而此后,透视法的应用历经数十世纪,才最终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艺术家们熟练自如地发挥。在此过程中,众多艺术家如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马萨乔(Masaccio)、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丢勒(Albrecht Dürer)等都对透视法则的研究和应用做出重要贡献,他们不仅在自己的绘画作品中留下透视法运用的实例,还为我们留下了从理论上探索透视法的手稿或学术著作,成为我们今人研究古典绘画透视法则的重要财富。
透视法的出现,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个重大科学发现,凭借这个发现,艺术家得以在二维平面上创造出逼真的三维空间。通常认为,布鲁内莱斯基是透视学的发明者。虽然在此以前,艺术家曾尝试过很多方法以暗示画中物象之间的空间感,但似乎收效甚微。而运用布鲁内莱斯基的方法后,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透视法来达到逼真的写实效果。可惜的是,布鲁涅列斯齐的透视实验作品已经佚失,我们无缘窥见其貌。但幸运的是,布鲁内莱斯基的传记作家安东尼奥·马内蒂在《布鲁内莱斯基传》(Life of Brunelleschi)一书中详细讲述了其透视法的应用效果:

布鲁内莱斯基在完成了他的洗礼堂镶板画之后曾向观众展示过其透视画法的效果——观众用一只手拿着一块30厘米见方的镶板画(此画是布鲁涅列斯齐刚完成的洗礼堂镶板画),通过镶板背面的一个小孔,观众能够看到真正的洗礼堂。这时,观众再用另一只手举起一面镜子,他从镜子里看到了完全相同的图像,只不过这个图像是镶板画中洗礼堂在镜子中的映像。通过这种方式,布鲁内莱斯基向现场的观众展示了自己的绘画技艺,画中的洗礼堂和真正的洗礼堂一模一样。

虽然故事中没有记述布鲁内莱斯基的具体作画方法,但我们能从中看出的是,透视法的应用的确极大程度上提高了画家的技术,绘画的写实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想见,这一发现会在艺术界掀起一股怎样的风暴!在普通人看来,这些艺术家们简直像拥有了魔法一样,能把任何物体原模原样地“变”到自己的画布上。
虽然布鲁内莱斯基的画作已经遗失,但他的朋友——另一位伟大的画家——阿尔贝蒂在《绘画论》一书中讲述了自己对于透视的研究和成果。《论绘画》是透视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学术著作,在这本书中,阿尔贝蒂在几何光学的原理上,对绘画的本质进行了重新的定义,提出了如何在绘画的二维平面上精确建构透视网格系统的操作方法,也由此改变了此前单纯凭借裸眼观察的画法。阿尔贝蒂的这种方法被此后的意大利艺术家或数学家称为“ costruzione legittima ”——“合法建构”。在阿尔贝蒂的诸多理论中,对透视法影响最大的是视觉金字塔原理,这个金字塔的塔尖就是人的眼睛,而画面就是金字塔的各个截面。
值得注意的是,阿尔贝蒂在书中提到了一种垂幕装置,这种装置是帮助艺术家掌握透视的重要工具。所谓垂幕装置,阿尔贝蒂在书中的解释是:它用极精细的纱编制而成,再用稍粗的线打上方形网格,最后把它绷在一个画框上。使用的时候,把这个装置放在画家和所画物体中间。通过这个装置,画家的视线穿过网格看到模特(或任何所画实物),帮助画家确定关键点在网格上的位置,就好像为模特身上的各个点标注了坐标。我们可以通过移动装置在画家眼睛与模特之间的位置,来调节入画范围的大小,但由于人的视力范围有限,所以使用这一方法作画,在构图上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阿尔贝蒂的书中没有示意图,在这里要感谢丢勒制作的这幅版画,通过这幅版画,我们终于不必苦恼于书中的抽象描述,而是可以清晰地看到垂幕装置的样子和使用方法。

虽然丢勒画中再现的装置不一定与阿尔贝蒂的垂幕完全一样,但我们至少可以借此有一具象的了解。这一垂幕装置的确非常巧妙,它为艺术家创作提供了极大便利,既缩短了时间,又提高了精确度,的确是一件非常实用的发明,肯定也是深受艺术家欢迎。
至此,透视法的研究和应用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不论是布鲁内莱斯基还是阿尔贝蒂,他们对透视的研究对于莱昂纳多·达·芬奇而言,都可归为“前人研究”之列而成为他的铺垫。因为莱昂纳多·达·芬奇对透视法的研究,真可谓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度,他以其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天才的头脑,不仅对透视法应用本身进行了彻底而深入的剖析,还对透视这一现象产生的科学原理做出了透彻的解释。他是公认的天才。

百年来,我们往往只知道达芬奇是个画家,而随着越来越多手稿的发现和艺术史家们的不断研究,我们惊讶地发现达芬奇在科学上的兴趣和成就甚至远远大于艺术。
正如前文所说,布鲁内莱斯基、阿尔贝蒂等艺术家对透视法做出的理性研究为达芬奇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和很多可供借鉴的经验。达芬奇曾在笔记中提到自己在1490年到巴维亚图书馆研读维帖罗笔记的事,仅在维帖罗的笔记中他就看到了八百零五条关于透视的结论。至于精通几何学的数学家欧几里得,更是达芬奇从少年时代就很熟悉的了。

莱昂纳多·达·芬奇一面研究前人的著作,一面自己实践进行观察研究,研究成果颇丰。他在手稿中的这些理论成果值得我们注意:
- 在定点透视中,画中人的眼睛必须和作画者的眼睛位置相同,否则物象就会发生形变,眼睛位置偏离越远,物象形变就越厉害。
- 几件大小相等的物体,如果第二件物体与第一件物体的距离等于第一件物体与人眼之间的距离,那么第二件物体的大小则只有第一件物体的一半。同样,当等大的第三物距离第二物与第二物离第一物的距离相等时,第三物的大小则只有第一物体的三分之一。若再按此规律放置四、五、六物,则依次按比例缩小。
- 当夜间,如果在房间中央点燃一支蜡烛,那么房间的四面墙壁都会映着蜡烛的影像。
由此,你能想到什么?
没错,根据以上实验,达芬奇总结出了暗室理论。而在后来的实验中,他的这一理论也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达芬奇在书中这样说道:
“如果有一建筑物的门面,或者一个广场、田野被阳光照肘,而对面有一间住房,你在这房中不对太阳的外壁钻一个小圆孔,那么房外所有被光照亮的物体都把自己的像传送过这个小孔,而在房间对面墙上(这墙应当刷白)呈现出来,一如原样,只不过上下颠倒了。如果在同一面墙上几处地方钻上类似的小孔,你从每一个孔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因此亮物体的影子全部存在于这墙壁的每一处,全部存在于墙壁的每一个最细小部分”,“这时你在这间暗室里靠近小孔放一张白纸,你就能在纸上看见所有的物体,形状与颜色都如原样,只是尺寸小得多。正是因为相交的缘故,这些物象都是上下颠倒的。这些从被照亮的地方射过来的影象,看去仿佛真是画在纸上。这纸必须极薄。要从背面观看。小孔必须钻在很薄的铁片上”。
这段内容清晰解释了利用暗室原理作画的全过程,在此基础上,达芬奇进一步记录了一个可供利用的方法:在物体前竖起一块透明玻璃,就可以在玻璃上描下物体的影像!
但这只得到了物体的轮廓,如何复制它的色彩呢?对此,达芬奇进一步解释说,
“你若是打算将色彩变化或消退的透视学用到实际工作中,可到乡间,选取相隔一百步的地点,例如树木、房屋、人或田地。取一片玻璃,牢牢固定其位置。眼睛也固定不动,观看第一棵树,在玻璃片上按树的形状画一棵树,然后水平地移动玻璃使真树紧靠着你的图画,然后在你的画面上着色,使得两者色彩与形状都极其相像,以致闭上一只眼睛看去,两棵树仿佛同是画在玻璃片上,并仿佛在同一距离。用同样的法子描绘纵深相距百步的第二棵树,第三棵树。这些图画能像助手与老师一样,帮助你画有关的图,并能使你画出的作品按正确的比例减退。”
这段表述为文艺复兴艺术家利用玻璃作画的事实提供了文献证据,事实上我们也确实在很多文艺复兴艺术家的遗产清单里发现了大量玻璃或镜子。仅是在卡拉瓦乔的家中就发现了十几面镜子,这应该是远远超出了日常生活所需的吧。

至于空气透视,莱昂纳多·达·芬奇之前的学者普遍认为介于人眼和物象之间的物质是一种消极因素,是一种“视觉欺骗”,而达芬奇却认为利用空气透视能够弥补线性透视的不足,这正是绘画之于雕塑的优势所在。达芬奇正是利用空气透视营造的微妙光影效果,画出了《蒙娜丽莎》中细腻的光影变化,为蒙娜丽莎胧上了一层神秘而朦胧的色彩。

写到这里,读者可能还对上述说法存有怀疑。为了论证莱昂纳多·达·芬奇的暗室说是否有效,我们可以借助英国画家大卫·霍克尼在2000年做过一个实验来验证。

事实上,大卫·霍克尼的实验初衷,是对文艺复兴画家利用透镜绘画的说法进行验证,但我认为这个实验也一箭双雕地验证了达芬奇的暗室原理。
实验中,大卫·霍克尼建出了一个类似暗室的小房间,然后在“墙上”开了一个方形小窗,窗子对面摆了一个凹面镜。大卫让朋友坐在窗外明亮的阳光下,自己则坐在暗室中的窗边,手里的画板上订了一张白纸。神奇的事情出现了,大卫手中的白纸上清晰的显现出窗外人的倒置映像,他可以很轻松的照着纸上的映像描摹下来,然后再进行后期的加工修整(如下图)。



这一实验结果是令人振奋的,它证明了暗室绘画的确实可行,也通过实践体验了“暗室+透镜”这一组合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使绘画过程变得简单快捷。可以想象,在古典时期的画家们在发现了这一方法后,他们也一定是欢欣雀跃、激动异常的,这必定是绘画史上的一次伟大的革命。
在另一个为验证凹透镜可靠性的实验中,大卫·霍克尼自己动手做了一架便携式相机,他给一个画架装上镜头和镜片并能够上下活动以便于对焦,再加上一块画板,最后用黑布把它们全部罩起来。实验不仅成功了,大卫·霍克尼还从中发现了一个规律,投射图像的清晰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光照的强弱,当光线强烈的时候,投射形体清晰,阴影深沉,高光明显,但暗部细节不够清晰。令人惊喜的是,这种特征也表现在了19世纪早期的素描中。仅仅是个巧合吗?
幸运的是,我们在一幅素描作品中找到了答案。18世纪的一位英国画家托马斯·桑德比,在他的温莎堡素描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作于相机中”。那么,还用再多说吗?这已经足够成为相机在绘画中运用的确证!

通过前面的研究和实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古典油画发展时期,艺术与科学总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绘画写实度越来越高的要求,促使艺术家们深入探索空间、透视、解剖的关系及其表达方法,科学思维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绘画中。很多画家会与自己同时代的科学家保持密切交往,甚至有些艺术家——比如大名鼎鼎的莱昂纳多·达·芬奇——自己本身就是科学家。所以,艺术家对先进科学发现有所了解并不稀奇,那么倘若发现了有利于作画的科学成果,为什么不能将其应用于绘画呢?正像发明了垂幕装置的阿尔贝蒂,他的这一发明就来源于自己早先发明的地平仪和视距镖。当艺术与科学相碰撞,一场革新也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事实上,随着科学的发展,艺术家们的绘画工具也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
当感性的艺术遇上理性的科学,艺术家将如何取舍呢?借助冷冰冰的科学仪器作画,又会不会有损绘画的艺术性呢?欢迎大家评论区讨论。
更多艺术八卦、干货、趣闻,尽在@扒点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