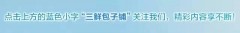宁波新碶头是我的故乡,过去隶属镇海县,现今改作北仑区。我虽属沪二代,但人生中的前三分之一时光在这里度过。从此地出去的人,包括他们的后裔,仿佛被一根无形的彩带系着,关注着这里的“格相貌”。记忆里的那些人,那些事,在经过岁月年轮的梳理沉淀后,越发的厚实与凝重。这就是“乡恋”的魅力,怀我同行共天伦。
北仑濒临东海,北临杭州湾,南临象山港。在远古时代,北仑是一片汪洋,后由于地壳上升,海水渐退,陆地始露。过去务农时,在太西涂地耕田,我还发现许多诸如贝壳之类的老古董呢。这里的地名也与海水搭边搭界,据我的观察,能顾名思义的地名有:镇海、小港、霞浦、高塘、坝头、塘湾、外洋、里洋、高潮;还有五眼碶、大碶、新碶、贝碶、备碶等。“碶”,就是用石头砌成的水闸。
改革开放前,故乡只能算是一屁股大的江南小镇,用当地人的话说:在太和桥上撒泡尿,可以浇遍全镇。这当然有点乱话三千,象李白诗中“白发三千丈”一样,谁见过有这么威武阳刚的人?但这个小镇里,每天在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大多相互认识,相遇时或点头示意,或热情招呼。东街头张家发生的事,第二天西街头的李家就知晓了。并不是陶渊明说的那样“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在新碶头,总有令你亮眼的特有风情:每当农闲,特别是夏天时,一帮子赤着膊,拖着木拖鞋,一手摇着蒲扇,一手捧着个伤痕累累搪瓷杯的中老年人,集中在桥头“嚼麦糕,讲大道”,可以把死人说得活过来,这些人被当地人称作“桥头老三”。我若呆在那里,一定也是个与生俱来的一副“老三骨气”模样。正象黄永玉说的:“鸟是好鸟,只是话多!”
“桥头老三”说的那些“骨头脑西”,虽然没有古人衣冠楚楚对酒当歌的儒雅,也没有现代人似是而非般的扮傻装酷,但他们有着对惬意生活的理解和追求。这种放松自如,闲情淡定的生活理念 ,与当地的生态环境密不可分。“桥头老三”也不是人人能做得,要有一定的阅历,有思想,有口才,还要有幽默与情趣,荤素搭配,不断创新;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阴阳五行,家长里短,八卦娱乐,就象万宝全书。而并非信口开河,拣到篮里便是菜。否则,人家会当你“特特糊”,死人讲拔棺材听——谁都不会相信你。
依稀记得儿时有首民谣:老公总司令,老婆宋美龄,是话勿相信,当地去打听。这当地,还真出了一些时代的牛人。
有句老话:隔壁做官大家喜欢,隔壁做贼大家吓煞!北仑男人聪敏勤劳,女人持家领导,夫唱妇随,最高生活理念是“循规蹈矩”。即使“俩家头”碰到不爽的事“造孽”,也是雷声大,雨点小:老公抓起一大把筷子,狠狠地由高到低往下掼,一记“忽喇喇!”接下来声音由强转弱,听听怕势势,隔壁人家以为在掼电视机呢。稍后“花花痒兮兮”,老佣回眸一句:“侬该只瘟寿头!”破涕为笑。“造孽”结束,和谐如初。
我跟你讲,北仑男人的“骨子里”对“老佣”勿要太好哦,舍不得打的。“作家”发嗲是闲情逸致,偶尔为之。不象北方某些渣男,自称大老爷们,看着老婆不顺眼,就会撩起巴掌,勒勒二个“嘴巴子”,打得来“喳喳西!”还文绉绉地装酷曰:掌掴。这正象周立波说的“喝咖啡的和吃大蒜的区别。”
男主外,女主内;男人要面子,老婆要夹里。旧时有首民谣念出了丈夫爱妻惜妻的情感:“燕子窝,朝南坐,人家来该打老婆,阿拉老婆勿打呵,辛辛苦苦抬来嗬;会补,补补裤,勿会补,就拨小人出屁股;会弄,弄弄饭;勿会弄,买岸馒头当当饭,省勒清咣清咣仗碗盏”。好一似,就象老鼠爱大米!有老婆在屋檐头拣菜,边拣边话老公:“小白菜,嫩艾艾,老公出门到上海,上海么事带进来,邻舍隔壁分点开,介好老公阿里来?”嘿,直白得“呒没闲话好讲类”。
北仑人爱“窝里厢”是有传统习惯的,民间俗语:光棍做人活神仙,生起病来叫皇天。家庭与光棍的强烈对比,使得北仑人害怕当光棍。你听“光棍经”这么念:光棍做人真伤心,日里三餐饭,夜到三块板;左手倒尿瓶,右手关窗门,冷水浸脚冷被睏;忖起大人勿抬人,眼帘会流脚后跟。”
一方水土养一方百姓,特别是餐饮文化。在北仑的家常“下饭”中,特色就是“不失本味”,追求“原汁原味”——鱼是鱼,肉是肉。如:白切肉、白斩鸡、白石蛋、白馒头等,不像上海、广东、苏州等地随便炒只什么小菜都要配上几种帮头,糖啦醋啦酱啦,还要拌菱粉,料理又放得多,结果吃起来鱼不像鱼,肉不像肉,哪里还分辨得出食物的原始风味?
提到北仑菜,宁波味,自然会想到“炝蟹”。它的地位犹如高大上的首席经济学家,大凡节头节面,婚丧嫁娶,宴席上都离不开红膏“炝蟹”这碗“大下饭”。上海人说:“迭能格”阳澄湖大闸蟹,五、六十元一斤,怀疑是不是被斩?北仑人笑了:“格相貌”红膏炝蟹,没有百来元一斤,老板!你是来勒打朋是伐?
过去农村耕种方式落后,做农民辛苦,经常出大力,流大汗。乡谚云:“三日不吃咸菜汤,脚骨有点酸汪汪。”咸菜又叫“咸齑菜”,在过去,北仑当地人把“咸齑”“蟹酱”“苋菜梗”视作三大“压饭榔头”。吃着这些“下饭”,胃口就会大开,拍着吃得急鼓鼓肚皮,也是一种幸福。
宁波人规矩重,约定俗成,男女有别。我跟你讲,女的,上不能爬屋顶,下不能“闹咸齑”,忌讳“过头鲜”,“闹咸齑”是小顽比的专利。腌咸齑有讲究,先将新鲜的雪里蕻菜整理,要卖的,不洗,叫燥腌;自家吃的,经晾晒后在河埠头洗净,往水缸里一层菜一层盐地叠放好,经过反复踩踏后封缸,静待一个多月的发酵成熟,香味四溢的咸齑就可出缸食用了。说来奇怪,这粗鄙之食,一旦与竹笋或黄鱼一起烧,就会起化学反应,合成谷氨酸钠,特别是烧作大汤黄鱼,就似“姜子牙遇文王”,鲜得来掉下巴。每当大人们说“咋介鲜嘞!”于是就忙接翎子说,这咸齑是我闹的!一副很有成就感的样子。
过去还有一种臭哄哄的下饭叫“苋菜梗”,就是宋美龄夫人踢碎数坛老蒋爱吃的这种臭食,但这没有妨碍她以身作则为抗日救国的热情。苋菜是上海人叫作“米西”的一种蔬菜,叶子有青绿和紫红的二种。苋菜梗就是苋菜生长到一米左右时老了的茎,经过与臭露盐渍后,和臭冬瓜那样有股臭兮兮的味道,对吃习惯了的人来说,是一种独特的美食。苋菜梗,属普通农家菜,尽管现在宁波人开的饭馆餐桌上,仍有咸齑菜和苋菜梗及臭冬瓜的身影,但毕竟是不稀罕的俗菜,与之相伴的生活方式已慢慢消逝,留下的只是深深的乡愁。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现在新碶头巳今非昔比,旧街道改建后成了北仑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移民到这里的“歪果人”越来越多,走在街上,已经很少有人认得出我了。然而,苍老的太和桥仍象颤颤巍巍的不倒翁傲视群雄,桥下的岩泰河仍细水潺潺,涛声依旧,就象流淌着的乡恋!
北仑的山,北仑的水,北仑的事,北仑的人,汇成一首歌,象邓丽君唱的那样:“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看似一幅画,听像一首歌,人生境界真善美……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