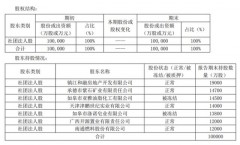刘诗古 林涵
鄱阳湖位于江西省北部,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在古代有过彭蠡泽、彭蠡湖、扬澜湖、宫亭湖等多种称谓。该湖也是典型的季节性吞吐湖泊,“春夏水涨,则一望汪洋;冬秋水涸,则各分界限”。长期以来,人们把“鄱阳湖”等同于早期文献中出现的“彭蠡泽”或“彭蠡湖”。然而,谭其骧和张修桂两位先生的研究表明,鄱阳湖在历史时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演变过程,“彭蠡泽”亦并非今天的鄱阳湖。本文认为,隋唐之际的鄡阳平原在经历多次水浸之后逐渐向沼泽与湖泊发展。至迟在唐中叶,在鄡阳平原的南部出现了一个被时人称为“担石湖”的水体,位于饶州与洪州之间,是当时人们往来的水路交通要道。唐代末期,“鄱阳湖”之名开始正式见载于史籍,并逐渐被当时的文人所接受,进而取代“担石湖”之名,成为鄡阳平原上各湖泊水体的总称。
虽然唐、北宋时期的所有地理志书都没有注意到鄡阳平原的水文变化,更没有任何记录表明北部的彭蠡湖已经向东南方向扩张,从而容易让人产生北宋时期彭蠡湖尚未越过松门山一线的错觉;但是北宋初期晏殊在《晏元献公类要》中已提到“鄱阳湖在都昌县南二十里”,可见北部彭蠡湖水体已越过松门山抵达鄡阳平原的西北部。此外,南唐徐铉和北宋赵抃亦多次在自己的诗文中提及路过“鄱阳湖”的情形。可见,《太平寰宇记》等北宋地理志书并没有及时反映鄡阳平原实际已发生的水文地理变化,而是有很强的滞后性。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唐中叶以后,鄡阳平原正经历着一个由局部水体向大水面湖泊发展的过程。

2020年7月11日,江西九江,航拍鄱阳湖中的鞋山。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 逼近历史最高水位。
今天鄱阳湖的基本范围,最早在北宋末期至南宋初期之间的史籍中才得到广泛且明确的证明,其南界在邬子港一带,西界则临近赵家围一带,东界已到达鄱阳县附近的双港,北界与今天相似,在周溪、四望山一带。至元明清时期,鄱阳湖南部地区相继发育形成新的汊湖,与此同时在滨湖地带人为地修筑圩堤,特别是明弘治与万历年间,在南昌郡守祝瀚与范涞等人的主持下,开辟了不计其数的圩田,水面湖田化现象日益严重,湖面日益萎缩。
在历史上,鄱阳湖区就经常发生水灾。目前较早的一条记录见于康熙时期的《鄱阳县志》,提及“隋大业三年,刘宗宏为鄱阳巡官时,三乡大浸,民以杀掠为事”。嘉靖《江西通志》对南昌的水灾有如下记载:“宋淳化元年六月,大雨,坏洪州城三十堵,漂没二千余人家。祥符、景佑、治平、绍兴、乾道间,皆大水,漂民庐,湮田稼,溃圩堤,人多流徙。淳熙、绍兴、庆元间,水灾如前。元至元、大德、至正间大水。”由此可见,宋元时期的水患时有发生,大水造成民居被漂没、田稼被淹以及圩堤被冲毁,居民损失巨大。
在明清时期,这类水灾的记录就更为常见。有明一代,南昌府“正统十四年大水。成化二十□年五月大水,漂民庐、人畜甚多,浸城门五日方退。正德元年秋七月大水,没禾稼。正德四年五月大雨雹,六月大水。正德十四年夏五月大水,六月宸濠反,启行大震电。正德十五年五月大水,没禾稼”。此外,万历十四、十五、十六等年,南昌等数县连续大水,低乡早稻尽皆淹没,秋季又干旱,晚禾尽行枯槁。为了救济,官府不得不开放河港,让大家自行捕鱼度日。可见明代湖区的大水不间断地发生。据张小聪、黄志繁的统计,在清代268年中,江西无水灾年份只有25年,其余243年都至少有一县有水灾的记载。在时间上,清代中后期江西水灾比清前期更为严重。在空间上,水灾呈现明显的地形特征,赣北鄱阳湖周边的九江、南昌、上饶等府滨湖地带,地势低洼,水灾最为严重。从文献记录看,嘉道年间的水灾尤为严重,几乎是连年大水,且就地域而言主要集中在鄱阳湖周边。道光十四年,从5月13日起,连日大雨,湖河盛涨,滨湖低处皆被水浸淹,连进贤县城也积水数尺。

《进贤县水灾蠲缓抚恤全案》
鄱阳湖区为何容易遭受水患?其原因在于“惟滨江低田,因上游水涨,江流宣泄不及”,即上游各大河流来水不断增加,下游入江口道宣泄遇阻,导致湖区水位迅速上涨。鄱阳湖是江西境内多条河流的汇集之区,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等五大河流皆注入其中,且地势低洼,滨湖人口众多。一旦流域内降雨量过大,鄱阳湖的水位就会随之上涨,但只要长江不发生大洪水,鄱阳湖的水就可顺利汇入长江,注入东海,不至于造成内涝。但如果长江水位也同期上涨,那么就会对鄱阳湖注入长江之水形成顶托作用,甚至形成江水倒灌入湖的局面。如此一来,不但鄱阳湖的水无法入江,且长江之水还会倒流入鄱湖,造成鄱阳湖水位急剧上升,很多圩堤无法承受压力,就会相继决口,酿成严重水灾。

县志中的鄱阳湖地图
既然历史上鄱阳湖区水灾如此频发,那么政府和民众是如何应对的呢?明清两朝都重视水灾的防治和救济工作,并有一套水旱灾情的信息上报制度。一旦地方出现水旱灾害,地方官员会逐级向上报告灾情,并寻求救济。在现在的第一历史档案馆,还保存有不少江西地方官员给皇帝上报灾情的奏折。对于上级官府而言,如何确定灾情的程度则尤为关键,往往需要派人查勘损伤人口、民舍、田禾的损害,圩堤的守护和决口等等,以此作为政府发放救济的依据。据张小聪、黄志繁的研究,清代官方的救灾措施包括蠲缓、赈济、平粜与借贷等。这些举措被统治者视为“皇恩”,但只能救一时之急,帮助度过危机,不能持续。
自然灾害的发生,影响民生甚巨。政府体谅民艰,一般会采取蠲免和缓征赋役的措施,减轻灾民的负担,尽快恢复受灾地区的正常生活与生产。张小聪、黄志繁曾细致梳理了清实录中的“蠲免”与“缓征”记录,发现赋役的蠲免一般并不能全免,而只是“十之几”。然而,就算是蠲免“十之几”之后,很多灾民依然无法按时完成赋役,于是政府会再次让步,对灾民积欠的赋役允许其“缓征”。但积欠年数久了,政府也就不得不蠲免了。顺治十三年,江西巡抚上奏称江西地瘠民疲,频遭水旱,请求按照直隶八府的成例,蠲免拖欠钱粮。这一请求得到皇帝的同意,批复“八年拖欠钱粮著蠲免”。“缓征”则是延期征收的意思,并不是不征。这些举措无疑都有助于减轻灾民的负担,从而帮助他们重建家园。
在减低被水灾民赋役负担的同时,政府在勘查灾情的基础上,对灾民进行必要的赈济。赈济一般分为两类:一是谷物赈济,二是银两赈济。嘉庆九年,上谕“江西省滨临江湖各县被淹田亩,惟德化县之桑落、赤松二乡,成灾七八分不等,其南昌、新建等县低田间有被淹,高田仍属有收,勘不成灾,被水之初即经降旨谕令抚恤,酌给一月口粮”。在水灾初期,灾民流离失所,赈谷的及时发放尤为重要。谷物赈济,基本上是以一个月的口粮为限。虽然上谕要求发给一个月口粮,但实际却要视地方上的财政状况而定,很多最后都变为了空头支票,灾民没有得到实际的恩惠。此外,银赈主要包括户部发公幤和官员捐俸银两种形式。这类记录在清实录和各类奏章中均有记载,此处不赘述。道光年间,鄱湖连续大水,进贤县向藩宪恳请拨发抚恤银,每大口受灾灾民折给银一钱八分,每小口给银九分。按户散给,使被水灾民得以糊口。除了拨给赈灾银两、减免赋税之外,政府还会推行“以工代赈”,雇请灾民修复和加固圩堤,兴修水利,恢复生产,并发给一定的报酬,解决其衣食问题。
“以工代赈”被视为应对水患灾害的治本之策,即可救灾民于水火之中,帮助他们度过生存危机,又可借此兴修水利,巩固堤坝,提高防洪能力,可谓“一举两得”。嘉靖《江西通志》记载:“刘涣,江陵人,成化间为鄱阳令,清慎廉明,爱民体士,治为江西最,筑圩堤以捍水患,长数千丈,得田数千亩,鄱民至今有赖,立祠祀之,因筑堤得暑疾卒,民哀痛如失父母。”可见修筑圩堤是滨湖人群抵御水患的重要办法。那些修筑圩堤的地方官,都被后人立祠纪念,可见圩堤之重要。以往的研究都认为,圩堤的修筑是为了围湖造田,但也并不尽然,有些堤坝修筑的出发点却是为了抵御洪水,间接为土地开垦提供了条件。
史载:“豫章为八郡水之所会,地最卑下,故田以堤为命。”豫章即南昌,是江西通省各大河流汇集之地,地势也相对其他地方低下,水田必须倚赖圩堤才能免于水患之灾。明代南昌邑人万恭也提到沿湖地区地势低洼,“水溢则大潴,水涸则鉅野,不可田”,很长一段时间内江河入湖三角洲都只是泥沙淤积而成的滩地。随着沿湖各县“生齿日繁,则与水竞利,夺而成壤”,地方官与当地民人开始在河流入湖口附近的低洼三角洲修筑圩堤,成田计数十万亩。不难发现,人类活动逐渐向滨湖地带扩张,为了防洪与围垦,不断人为修筑堤坝,但与此同时也压缩了湖区面积,降低了蓄水能力,增加了水患发生的可能性。
从目前遗留下来的文献看,明代前期鄱阳湖地区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圩堤修筑。清初新建邑人赵曰冕在《重修大有圩牛尾闸碑记》中称:“惟湖之有圩,由郡守祝公创始於弘治十二年,世因其利,厥后屡圯屡修。”即鄱阳湖地区的圩堤是由南昌郡守祝公创始于明弘治十二年(1499),此后世人受其利,屡毁屡修。弘治十二年南昌“岁饥”,祝瀚发榖募民修筑圩岸,跨南昌、新建二邑,南昌境内圩堤六十有四,新建境内四十有一。 其中比较大的圩堤有“大有圩”,“西始石亭庄,东抵牛尾坽,延袤四十里,北障大浸入鄱湖,而南垦平田数万亩”。赵曰冕曾称“大有圩”内有田数千万亩,“夏税秋粮几占邑册之半”。明弘治年间是文献记载中鄱阳湖地区第一次大规模修筑圩堤,方式是“发榖募民”。
万历十四、五年,鄱阳湖区连年大水,南昌知府范涞联合南昌知县何选、新建县知县佘梦鲤,请於院司道发赈灾银一共7600两有奇,在南昌县筑圩138处,新建县筑圩174处,并修石堤、石梘、石闸若干处。这是鄱阳湖地区第二次进行大规模的圩堤修筑,依然是由官方主导,以赈灾银募民修筑,不仅活饥民以万数,并且修堤扩土,一举两得,视为“永利”。在这次的修筑中,有许多是对旧圩的修复,如前文提及余家塘等三圩决口,就是在此轮修筑浪潮中采用了“捲埽”的办法堵塞了决口。此后,圩堤之修筑更为频繁,万历三十五年新建知县吴嘉谟发抚院义仓谷修圩160处,第二年南昌知县樊王家动用仓榖修圩185处。除了南昌、新建两县下游低洼地带大量修圩外,进贤、余干与鄱阳等县亦在此时期修筑了大量的圩堤,开辟出许多新的圩田。很多圩堤其实就是在“以工代赈”的名义下修筑的。
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主导下,大量的湖池水面被人为修筑的堤坝阻断,把江河湖水挡在外面,内部开发成可以耕种的圩田。明中叶以来,这一持续的人为湖田化过程,以及江河泥沙在湖区的堆积,加剧了鄱阳湖水面的萎缩。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堤坝其实扮演着两种矛盾的角色,既起着抵御水患的作用,又是造成水患的重要原因之一。魏丕信很早就提及湖北江汉平原及其周围有一个“水利循环”:一方面人类通过移民、开垦低地、建设堤坝等,水利得以扩大;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对环境的压力、政府治理的衰退、基础设施维修困难、私人侵占与非法开垦,水利出现衰退,水患危险加剧,水灾影响扩大。
此外,古代人把水灾视为是一种被称为“蛟”的东西所为,所以“除蛟”也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水灾应对措施。敕封地方神灵是朝廷在水患中彰显自身权威的另一种方式。在鄱阳湖区许逊(当地又称许真君)为民斩蛟治水的故事流传甚广,并于正统元年被列入朝廷祀典。该信仰出现的社会心理大概来源于此:每遇大水,易坏的堤坝往往从底部开始崩解,造成管涌现象冲入圩中。在时人看来,“水患”就成了“蛟患”。有文献称:“其曰蛟者。南昌,泽国也。相传多蛟,螭窟其下,蛟所在岸乃善崩”。因此,擅长斩蛟的晋旌阳县令许逊被奉为一方神灵。水患之频发,使得人们以“伐蛟”为防灾之急务。
乾隆五十一年,南昌知府张若渟向朝廷奏请“伐蛟之令”:
复查春秋大雨时行深山穷谷,间有起蛟之事,是以江西士民咸崇信晋臣旌阳令许逊,因其修真悟道,术能致雨,兼能伏蛟,曾着灵异,在在俱有祠宇,而南昌府乃其故居,尤庙貌蔚皇。臣等亦循旧,于岁时率属瞻礼。虽相传伏蛟之说稍渉渺茫,而庙之附近地方向无此患,似亦理之,或有可信者。至伐蛟之法,询之老民,亦能知晓。兹臣遵旨饬属督令保长、乡约人等,随时留心,于深山草木、不生霜雪、不积之地,预为挖除,以为防患未萌之计。
对此,乾隆皇帝有御批:“江广一带每于大雨时行,间有起蛟之事,深为民害,自应搜寻挖除,防患未萌。”在很多文献中,蛟是藏在深山之中,并不出现在平原和堤坝,类似于现在我们说的“暗涌”。张小聪、黄志繁曾专辟一个章节对“伐蛟”进行讨论。他们认为,民间对可导致水患的“蛟”充满恐惧与厌恶。从实用或工程的层面看,伐蛟之术对水灾防治没有任何意义,人们却可借此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寄托某种希望。不过,当时人似乎都相信,水患的形成是因为有蛟的存在,如果能把蛟找出并挖除,就可防止水灾的出现。于是许真君信仰广泛存在于江西各地,特别是鄱阳湖区,有其特定的自然与社会背景。
至此,鄱阳湖区的水患一直存在,长期困扰滨湖人群的生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大水,呈现不规则的周期性,且有连续几年大水的情况。从宋元直到明清,历史文献中关于湖区水患及其应对措施有着诸多记载。历史上鄱阳湖的面积比现在大很多,随着人类不断向湖围垦,把很多原来是湖的地方,围垦成了农田或者内湖,湖区面积一再萎缩。明清时期大量的堤坝相继建立,缩小了湖水可宣泄的范围,水患灾害持续加剧。人类活动不断向滨湖一带扩张,农田村庄众多,堤坝林立,使得上涨的湖水无处可去,水位必然一再升高。只有到了万不得已之际,才会决堤泄洪。1998年大水之后,退耕还湖的呼声很高,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湖泊河流的蓄洪能力,增大湖区的蓄水量,从而减轻洪涝灾害。此外,1998年大洪水之后,很多滨湖村庄被淹没,政府采取了移民建村或建镇的方式,把大量的低地居民迁移至高地重新建村或建镇。事实上,如果没有这次移民建村行动,后来湖区的压力可能会更大。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