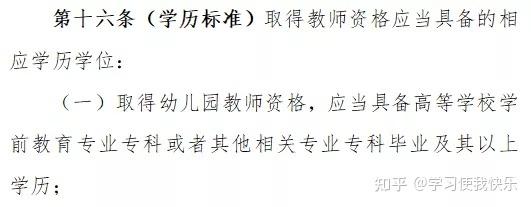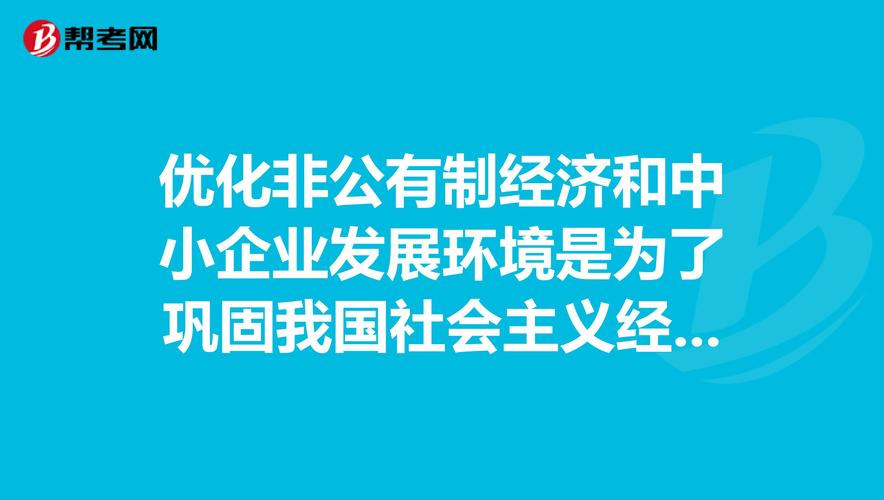七堇年。我初高中时代非常喜欢她,她的每一本书、每一篇随笔、散文我都看过,曾经还有专门的只摘抄她一个人段落和语句的笔记本。
她是那个时期影响了我的心境和语言风格作者。在那个青涩年少又没什么见识的特殊时期,她文字下的女性美,那种坚忍、张力、决绝和静气都一度让我深为着迷,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认为所谓的严肃文学就是这个样子的…她推广的作家简桢、黄碧云、安妮宝贝、王安忆、张爱玲…我都一本本地看完。但最后我明显发现了不对劲,就是她们的女性意识与痕迹,都太重了。
而且相比之下,七堇年的语言和叙事风格甚至还没有走出自己的体系和回路,她还太嫩了,就像她自己在《远镇》里写的那句对“父亲”说的话一样“你对于我太淡了”。但是没关系,最初发现这一点的我想:七堇年还年轻,年轻是优势是武器,她总有超越的可能。”
然后直到读完《澜本嫁衣》后我终于彻底地释怀了,是的,就像她在文中借由叶一生对知秋的那段独白:“我对叶知秋的揪心和鄙夷难道不过是一场左右逢源的嫉妒:我既没有那些风华精英的骄人成绩,又不能如她这样以一个小女子的魅力安然享受一个又一个男人的追逐和抚摸——且不论这追逐与抚摸的真诚与否。
我的失落在于我一无所得。”
七堇年其实一直在走她自己的路,但是这条路的形态就如文中的那段话一般,被规定被束缚而无法有除了摆出反抗以外的姿势或干脆眼一闭一路走到底就靠骗骗初中、高中女生吃饭算了。
事实上回过头来看,七堇年其实也一直只是在摆出反抗的姿势罢了,从《大地之灯》,从《被窝是青春的坟墓》。一直都是。因为她既没有切实的力量和切实的反抗目的,也没有将自己放在更下位的表现形式的认命的自觉。所以她就只能一路表现出一副倔强的、梗着脖子不肯屈从的姿势描绘流年浅草间已逝的,且再无新意的青春故友、故事,因为除此之外她已没有内容可写。
她的问题是,她已经从很早之前就在开始一个重复的怪圈,反反复复写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套路,一模一样的转折,一模一样的用词,一模一样的语言,一模一样的自白与一模一样的留白空间。
或许她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她又总在不认命地挑战一些新的题材——遗憾的是,也仅仅只是题材而已。
曾经被多少像我这样的因偏执而不明的小读者高看了一眼便陡然升起万种期待性的错爱——本就是我的错。所以我不会说:“啊,七堇年也就是这样么,比我想象中的差太多了,好失望”这样的话,完全没有,她其实已经是个很不错的写手了,是她团队的各种打造和包装让我一直会错了意,或许会错意的也不仅仅只有我而已。七堇年终归走的是一条已经被前辈们挤爆了的“自己的路”,像简桢,像黄碧云,更像安妮宝贝,但又都不是。但又是因为如此,才导致了她的路的狭窄。
她成在她的年轻,也输在她的年轻,她向往去走的路,已经被前辈们用更扎实优雅的姿态给铺垫结实了。
素净化旅行,强迫症般地描述细软,被小资的名号涂抹得严严实实的丽江山水、藏地风光、古镇风情……这些公式一样千篇一律又行情大好的关键词,因为横空一个安妮宝贝而全部照单全收了——这是网络文学刚打起头阵的那几年才可能发生的现象,往后的吃螃蟹者无一例外地都被打上了前者的影子,被盖了光和泛滥得失了势。
这也是为什么这世上只有一个安妮宝贝,但是却可以有无数个七堇年。太多的那个必然会被弱化,一样的路,未必能一样地走。记得大大前年的时候吧,无意中在书店里看到了《尘曲》,原来都已经上市一年了,还是自然而然地买了一本,回去翻了翻,读到一半终于还是合上了。大概无论我再怎么想回味、探索能连接起过去时间线上的那个我的心情的甬道也是徒劳,就像我那套已经堆在书橱地下吃灰的陈绮贞的CD一样,“带不走的留不下的让大雨侵蚀吧”。在某个节点上我也正式明白了,这类被特定的“青春小说”,泛滥的女性意识,大概对我来说已经永远划上句号了吧。毕竟我也老早就不是那个化学实验课上偷偷塞着耳机和同桌聊天,对着做不完的题还会偷偷冲着老师的背影做鬼脸的15、6岁的高中女生了。人总是在成长呀,但是在这段重要的成长过程里我非常感谢堇年你能以这样的方式加入,送给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无比宝贵的力量,再见,如你所说——“若没有离别,成长也就无所附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