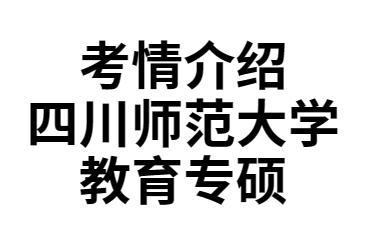齐宣王的“以羊易牛”成为孟子人性论证的重要道德经验。孟子与齐宣王之间围绕“以羊易牛”的对话,揭示出同情、不忍和行善是仁慈的结构和发展阶段;仁慈的本质是隐性的自爱。齐宣王“以羊易牛”的过程包含了仁慈与公正的冲突,以及特殊仁慈与普遍仁慈的矛盾。
(齐宣王)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闻之胡屹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编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
“以羊易牛”同“孺子将入于井”的思想主旨都在于经验地论证仁慈的先验性。齐宣王舍“将以衅钟”之牛,“以羊易之”。百姓视之为“以小易大”的吝啬;齐宣王也深感“是诚何心哉”。但孟子点出了其本质是“无伤”的“仁术”。齐宣王的困惑表明,其行为不是依循现代西方功利主义和康德式道义论规范指引的理性化产物,而是源自内在固有的仁慈的道德本能和道德直觉。尽管齐宣王所置身的争战杀戮的时代和所位居的攻城略地的角色,决定了仁慈被压抑的命运。但是,仁慈作为一种道德本能,不同于道德习惯。道德习惯可以因外在情势的改变和行为的重复而培养或者消除。但是,仁慈可以因情势的改变而被压抑,无法被消除。假以适当的外在导引,那么,它就会被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