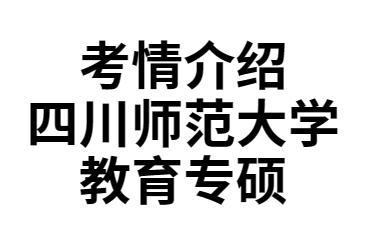他叫方圆,个子不高,长的结结实实的,略黄的长头发遮掩着带着稚气的脸庞,俊俏的鸭蛋脸上,一双黑黑的葡萄眼睛,很是秀气,略翘的小鼻子底下的嘴片也是翘翘的,可惜就是脸皮黑乎了点,粗糙了点,不然比人家姑娘还秀气呢。 方圆挺可爱,干啥都很卖力,有时我们衣服破了,找不到针线,向人借时 ,别人总是唠唠嘴:那儿,方圆有!确实他有,而且叠得很认真,针上的线儿都穿的好好的,甚至连疙瘩头都结好了,我们借针还得借人呢:喂,方圆来一下,实在不行。他没有答话,露出白白的牙齿轻轻笑笑,然后带着调皮的口气说:讲的倒轻巧,我补行啊,拿什么报答呀?话还没落音,我们已把破衣服,针线连拿带哄塞在他怀里,好说,一瓶汽水吧!绝对算话。其实才不绝对呢,即使你诚心诚意买点东西给他,他死活也不会收。 在这些外流工的班子里,论年龄要数方圆小,论资历,可以算得上国老元勋了。 方圆今年刚满二十岁,外流工的大潮过早的把他卷入其中,他先在合肥做过泥水工;后到祁门当过垦林员;在北方的列车上扛过包,在南方的码头上下过货;对于外流工的酸甜苦辣,已不那么敏感了,司空见惯了。 没有亲身体会外流工生活的人们,有谁知道其中的艰辛与屈辱啊!自中国农民工大潮诞生已来,他就随着这股洪流,打着包袱出门去了。 今天,他又转战在这车声嘈杂,尘灰飞扬的公路上了。一年四季干外流,长锹只剩小锹头,年青人变小老头......短短几句,无不反映出外流工生活的一斑。 六月的天气骄阳似火,也正是浇柏油的好时节,我们已浇完一千米大寸子路面,现在开始油分子揭面了,分石子只有指甲盖大小,公路站的人都叫瓜子片子,瓜子片封面,比铺寸子还麻烦些,铺寸子只需把车子运来的石,沿路打成长长的垄埂,然后由四轮车拖着熬滚的柏油大铁箱,两轮卡在垄埂上,向前边开走,边放油,后面紧随着八人铲拌,使石料粘油均匀即可,分子封面却有所不同,先得在大的铁板上加热铲均匀,后用四轮运送到先期的寸子路面上,铺撒,整平后用压路机碾实。分子揭面是公路尾活,公路站的一些领导也和我们一起冒着炎炎酷暑走上工地,既是查看,也是也督促。我们带班的头儿为能在领导面前表现一下,吆喝着,鼓噪着......头顶是毒辣辣的太阳,路面上是微微跳动的蜃气,奇热的天气,又是出奇的卖力,一气下来,一个个象是从水锅捞上似的,湿透的身子,仿佛彭涨了,溶化了,就连那天上的太阳也变得昏眩蓝绿,整过大地简直是纹丝不动的热窑。高高的熬油平台上,沷撒的柏油,溶化渗染着,发出让人烦腻的光亮,平台上烟囱的淡烟与地面蜃气相接映,把平台上的搅油人衬托的更加让人怵目惊心:长长的瓢把慢慢的搅动着,没带草帽的脸,紫红,紫黑。脏弄的长发被汗水浸湿,一绺绺粘贴在额头上,一身黑乎乎的工作服,一座黑乎乎的熬油平台,以及那平台上的熬油人,那景象不免让人担心,会不会一同在这白刺刺的日头下,蒸腾了,挥发了。 再看这些铲子的,长长的铁板上,两板车瓜子片石料一倒,打垄,浇油,人们立即铲拌起来,两人配合,共四人,一班迅速翻拌到头,去烧油锹,下班立即上阵,刻不容缓,上翻下落,左来右去,快如流星,往复三四次,灰多的还要多拌几次,翻好后,马不停蹄,打垄,装车~ 炎炎的烈日,扬起的尘土,把整过工地上的人都严重丑化了,为防柏油粘染,一个个不知从那里弄来破旧衣服,裤脚用细带扎紧,活象一群打着绑腿,衣着褴褛的讨饭人。汗水顺着脸脥流淌,用手一揩,褂袖又是一片湿,衣服汗湿,蒸干,蒸干又汗湿,白沙沙的盐渍无规作的洇开,开成一幅色彩斑斓的地图。 中午,吃饭还不到半小时,有的连茶水都没喝好,紧张繁重的体力活消耗大量水份,一个个都焦渴得难以忍受,但大家都强忍着,期待着......公路站的领导来时那份认真的劲儿渐渐软化了,且都七长八短地到阴凉处避暑去了,只有施工员一人继续留着监工,工人们依旧拉着石子,打着长垄,添着烧锹的火堆......猛然之间,平地一声雷:我日他妈的,铁饭碗啊!只见方圆把脸一拉,锹一拄:要不是在家蹲着骨头痛,怎么到这路上受刑!施工员的脸色也在方圆的话语和动作间,微妙而又难以觉察的由阴转晴:哈哈!这个方圆,油腔滑调!也许是这话的刺激,也许站上动了测隐之心,立即传话,全此休息一会,喝点水再干。 太阳好容易,好容易才变红,变凉。一天紧张劳累的工作结束了,大家争先恐后地拦车回家,我们十来个扒车利落的提前走了,剩下的人只得随道班的小四轮了。 我们前面回来的人,都洗过脸,正吃着晚饭,后面的人才陆续回来:今天真走运,方圆捡到一只三脚狗,随声看去,后面的方圆正从工友手中接过自己的铁锹,邋遢破旧的怀中正抱着一只黑白相杂的瘦瘦小花狗,是那小狗样子太寒怆,还是方圆过份爱怜,竞在他的怀里服服贴贴的依偎着,仿佛失散的孩子,终于找到自己的父母,方圆放下小狗,大家围过来七嘴八舌地评价起来:这么丁点大,这么瘦,不知断奶没有,我看养不活!唶,好难看,甩掉算了!.......方圆没有辩白,只是在小狗面前拔点饭,小狗先是不动,只是坐着,身子一颤一颤的,那样子分明是害怕。后来到底经不住米饭的诱惑,前脚动了动,挪离一下身子,开始走动,原来真是三脚狗,一只前脚总是向上提着,一颠一颠的,走到饭前,白老瓜子黑觜团向地下一贴,狼吞虎咽地摸索着饭团,哎呀,是饿坏了,怪不得变成这个样子,只要是饿的,养活还是有希望的,方圆看着很高兴,黑黑的脸上绽出无邪的笑容,他看地下的饭吃完了,又拔添了一些。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小狗的脚也好了,身子也长的油滑光亮,往日那瘦骨嶙峋的三脚狗,已出落成活沷,健壮,聪明而又十分讨人喜欢的花花了,花花就是小狗的名字呀。方圆常这么叫,我们也听惯了,顺口了,每当花花不在家时,只要连喊几声花花,花花!一个朴朴跳跳,摇头甩尾的小淘气,就立刻跑到跟前。花花啥都好,就是有点讪脸,休息的当口,我们坐在床沿上,无意间踏动双脚,这时花花不知从那里疯疯颠颠撒着欢跑来,两脚向前一捺,抱抱这个脚,拽拽那个裤脚,又是打滚,又是用牙咬。不动还好,一动,它更来劲了,即便你把脚高高抬起,它也踮着两脚抱着不放,如果不声色俱厉地吆喝它,那股疯傻劲才没完没了呢。 花花虽说淘气点,但确实逗人喜爱,你看,黑乎乎的嘴团,短短的,圆实实的,只有唇边每根细长的胡须底下有一个个菜子大小的白点点,大大的脑瓜上耷拉着两只软软的大耳朵,再加上短短的,胖胖的腿儿,以及一双厚厚的,揸揸的,如小蒲团似的脚掌,看去似乎有点朴拙。 花花渐渐长大,也渐渐和许多人混熟,除了平时跟方圆跑进跑出,有时晚上去塘边洗衣服,花花也蹦蹦跳跳去为我们作伴。 阴雨天来了,工地不能干活,这倒成了训养花花的好时机,训手的主角当然是方圆了,他要花花前脚伸直,两眼专注地凝视前方 ,不许它随便东张西望,开始花花很不耐烦,就是不愿意,几经周折,花花便安安静静地随人摆布了,瞧,那副可怜的模样,就象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人多花样也多,什么小狗扒板凳啦,钻圈圈啦......不一而足。 令人高兴的是:一天夜里,花花突然奶声奶气的叫了两声,狗大自咬,是呀,花花该长大了,在这以后,人们逗它玩时不时撒着欢叫上几声。 组里要为其它工地突击一段时间,留一人照应即可。一早,接人的汽车便来了,一个个拖锹,扛镐头,一窝蜂地扒上了车厢,汽车正启动时,方圆突然用力急促地拍打着驾驶室头顶,大叫驾驶员停车,那十万火急的状态,把一车人都弄的莫名其妙,面面相觑,只见方圆一个飞机跳伞的架式从车厢蹦下,撒腿跑回家中,不一会又上气不接下气地扒上了车,开始大家以为丢了什么车西,一问真是啼笑皆非,原来忘了和看家的打个招乎,每天吃饭别忘了花花。突击一段时间回来一看,花花果然长的更壮,更圆,更漂亮。 这段工程结束了,又要搬家了,东西都好带走,大家担心的就是花花,送给当地人,一个个又舍不得,把它带走还得坐车,房子里的东西都叠得一干二净,平时非常热闹,拥挤的房间,一下变得空旷冷漠起来,花花象感到什么似的,只是在空空的房子里不安的走动,或是圈坐着,有几个试图把花花抱起来,可是一碰就跑,即使勉强抱起,不是摆动身子,就是用牙咬,为此,大家建议方圆去试,说来也怪,别人抱不行,方圆抱,它倒一动不动地伏在地上,任凭他搬起,搭在肩上 ,不逃跑,也不啼叫,只是身子瑟瑟发抖。一路上花花很是顺从。到了新地点,花花变的拘谨胆小了许多,不再象以前那样撒沷,机灵了。方圆安顿好行李,挖了半碗饭给花花吃了,这时我们唤它,它又向我们摇头摆尾了。 又过了几天,花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偶尔有陌生人来此,它就叫个不停。工地上的石料多起来了,站上要求抽调两个人夜里值班,可是就是派了人,还是丢失了不少石料,因此大家都建议方圆带着花花一起去值班,是巧合,还是花花功劳,自从花花去了后,石料丢失现象就没在发生。花花也就更受人们喜爱,方圆也为有这样一个花花而骄傲。 一天下午我们刚收工,忽然听到有人叫:不好了,花花吃药快不行了!我们乍一听,谁也不信,上会儿还是活活跳跳的,这会儿又喊吃药不行了。我们跑去一看,傻眼了:花花发疯地叫着,打着滚,嘴巴一张一噏用力在地面甩动着,门牙磕掉了,血里杂着白沫从嘴里一撮一撮揉映在地上,光洁油亮的身子,被重重的泥土包染着。快,快搬去喝点水看看怎么样。六神无主的方圆好象猛然清醒了,不顾一切地扑向花花。注意点,别让它咬了!有人提醒。方圆不管这些,抱着花花向水沟跑去。花花喝了几口水,不在象以前那么挣扎了,这时又有人端来肥皂水嚾了一些,花花掀了掀身子,没有掀动,又打了几个嗝,没有吐出,接着甩了甩蒲团似的脚掌,睁了睁变硬失神的眼睛,动了几下,便再也不动了,方圆蹲下身子,用手轻轻抚摸着死去的花花,一泓盈盈的泪水再也蓄积不住,猛地用手一揩,方圆哭了,哭的很伤心。 第二天,方圆任性要返回家乡,我们再三挽留,劝解,他才说:我的心很难受,也很想家,过一段时间再来吧。 ________________本文初稿于安徽和县西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