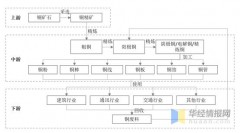我还是那个为亲情赎罪的丹丹,但我的世界大得很,所以赎罪只算我人生面包里的小小一撮酵母。
只可惜电影太短,屏幕太小,你根本不会注意到,从我家逼仄的楼梯跑下去溜一圈,会见到怎样的人,听到怎样的事。

01.
父亲是1979年底回天津的,其实在此之前他早已释放,那是1977年底的事了。这中间的两年他干嘛去了,无从知晓。反正那个年代,很多事都可以变成隐私,反正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问不问都一样。

他回来之后,很多事都像干白菜一样晾晒到光天化日之下,包括我是他女儿这个事实,似乎也在街坊邻居之间被重新普及一遍,变得人人皆知,包括那些刚会算加减法的小毛孩。

每次从毛纺厂回家,我都会路过一家瓜子摊,偶尔在他家买瓜子,为的是让父亲有点零食可供消遣,让他磨磨多年来因为不刷牙而几乎坏透的牙齿。
父亲近些天什么都敢吃,软的硬的,咸的辣的,通通笑纳,颇有点破罐子破摔的壮烈,他笑答:“索性掉光,好装假牙,你妈瞧着还能顺点眼。”

卖瓜子的摊主家有个聋娃娃,据说因为高烧没及时看,才变聋的。那小男孩长得童子相,带着灵气,一双大眼睛星光闪闪如夜之晴空。我有时想,真羡慕他的无忧无虑。

我有时幻想和他交换耳朵,这样就可以不用听周围邻居大婶的窃窃嘶吼。没错,是嘶吼,而非私语,因为她们的音量完全可以用来吆喝卖菜卖水产。
02.
一个大婶叨念:“三楼姓冯的那家,男人回来了!听说这次不是自己跑出来,是政府特赦的。”另一个疑惑地问:“真的假的?不是在里边呆了20年了,居然能活着回来。”“活着怎么了?兴许过几天又进去也说不定呢!你想,他脑袋上那么大一顶帽子,今年摘了,明年还能重新扣上。”“哎呀,也挺倒霉的。”

这时我走近了,她们低下头继续谈天说地,表情显得中庸而无害。

因此,父亲的释放并没有让所有相关和不相干的人原谅我们,冰释前嫌。相反,他的真人出镜让我家的政治面貌愈发清晰,就像马路上擦不净的标语一样,尾大不掉。

就连我找个对象,都变得比登蜀道还难,因为这段“蜀道”已经被周遭群众的唾沫淹没,即将垮塌。
这些唾沫是洋葱味、椒盐味、拌菜味或者肥皂味,但不是铆焊味、木工味、尘土味或者机油味,总之,是阴柔缭绕的女人气,而非坚定铿锵的男人味。
某大婶最大的兴趣,就是布下天罗地网,在我的恋爱和婚姻里留下自己的爪痕01.
诚然如题,1950年出生的我,在宝贵的婴儿期、儿童期、豆蔻韶华以及之后的青春年华,一直都是一个被“公平对待”的女子:无论女孩还是男孩,对我都是一视同仁地鄙夷,唯恐避之不及。
直到1980年,我终于荣幸地成为毛纺厂数一数二的女光棍,孑然一身,潇洒倜傥,人尽皆知,名声在外。

我并没有端着大喇叭喊话“我是女光棍”,但我的情感处境连同家庭背景,早就被无数条闪电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传遍厂区的里里外外。恐怕连墙角的老鼠缩回洞口,见到老鼠女王第一句话,都是“那个女光棍又是自己上班自己下班的,没人接送她”。

因此,我更加憎恶这些语言不通的鼠辈,每个星期至少带一次早点,送给院门口的母猫,希望她吃饱喝足,好好养胎,多生养几只小野猫,把那些吱吱作响的坏老鼠做掉,好替我出了这口恶气。

令我失望的是,母猫喜欢独来独往,对主动送上门的公猫并不买账,她似乎更喜欢享受屋檐下的懒懒暖阳,翘起尾巴舔舔毛发,做做卫生。
其实这样也挺好,倘若一窝小猫出世,她就要下岗照顾猫仔,夙兴夜寐,废寝忘食,哪还有心情舔舐自己,取悦自己,独霸这片厂区?

02.
根据我的推测,假使猫有8年的寿命,那她抚养小猫的时间至少要占到半年,加上怀猫仔的3个月,算下来,她要花费生命的十分之一才能应付这一系列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嗨,小猫长大拍拍屁股就走了,压根不会感恩老猫,不像我。

因此,我和这只母猫算是同病相怜,渐渐成了朋友。
每天早上,我都会不自觉把这些思绪快速梳理一遍,到后来,竟然提速了,一个念头闪过去,这份仪式就算圆满礼成。

因此,每天上班的心情都是好的。然而,下班的心情却不甚相同。
03.
每天下班都会经过一条长达50米的小胡同才能辗转上楼,走进去,路过许多房门,能将多家小平房清点一遍。

第一家的女主人身穿一件无袖白底蓝碎花纯棉背心,正在厨房门口跺菜,当当当,山响。第二家的两口子又因为赌钱的事吵起来了,啪啪肉搏的声音清晰可见,估计又是女主人取胜。最后一家的张寡妇嘭地开门,一盆脏水哗啦落下,真是手脚利索。
我跺跺脚,试图将溅在脚上的脏水渣子甩掉,至少哄哄自己这颗不悦的心脏。

当然,她们于你来我往之中,不忘见缝插针谈论国家大事,“是,就是东边那家的老姑娘,可不嘛,没嫁出去呢!”“估计没人给说媒,听说她家祖上是当官的,亲戚都跑到外国去了,大概也是为了躲着她们吧!”“哎呀,亲戚都不管,看来这老姑娘注定要老在家里头了……”

“哎呀”两个字自带天津卫一股抑扬顿挫的高山流水味道,用在我身上,却有着不大不小的杀伤力,这杀伤力刚好可以把晚饭食欲减半,帮我瘦下来。
时局是把双刃剑,架空了我的终身大事,却保全了我的自由01.
虽然我是靠在毛纺厂早出晚归辛苦劳动吃饱饭,但在内心深处,从不把自己与那群多嘴多舌的女人划归到一个物种。
有两个大婶,她们倒是打听过我的心思,问我找对象有啥要求。我说过得去就行,结果后来还是不了了之。也许没人愿意和我约会,也许是她俩借说媒之名,行刨根问底之实。

我隐约觉得,比起每天关心东家长李家短,似乎还有更有意义的事情等我发掘。
02.
1980年30岁生日那天,父亲给我准备了一个生日蛋糕,里面放的是砂糖,吃起来颗颗糖粒像砂纸一样打磨着口腔,甜得齁嗓子。薄腻的奶油像一场春雨,稀稀落落地覆盖整个厚重的蛋糕胚,但我宁可齁死,也要多吃几口,以解馋虫之痒。
他出狱后,竟然获得一定的退休金,而这些钱中,势必有一部分会变成美食钻进我嘴里。这个蛋糕似乎施了法,吃了它,我一下子长大了,变得泰然,变得自若,变得浑身有力气。

那几个为数不多的女邻居像是潜伏在房子周围的毒蝎,有意无意,玩着闹着,就会蛰到别人。
而此刻的我已经负负得正,变成一个无坚不摧的甲壳虫。那些闲言碎语,那些流言蜚语,如今只是个无壳的软蚜虫,分分钟就可碾压掉,手起刀落,不留痕迹。

03.
我似乎也不会因为厂里那个时髦小流氓一声吆喝,就吓得屁滚尿流。那个家伙我不熟,从别人口中隐约得知,不是姓尤就是姓暴,不是叫胜就是叫利。这号人物,说穿了就是个自以为能上树的纸老虎,一捅就破。
真有一次,早上上班,见我手里拿着打包纸,纸上渗着油,他像一只蜿蜒前行的壁虎,甩着长头发凑上来,热络地问:“丹丹妹子又来啦,手里拿着什么……好吃的是吧?你这是怕哥饿着,给哥哥我准备的呀?”

这次我没有跑开,因为这个活物似乎就以吓唬女孩为荣,我不该怕他。
我站定了,把草纸摊开,嘴一斜,脸一横,笑道:“看好了,茅房用过的草纸,早点吃剩的唾沫星子,沾着几块玉米饼,喂猫的。您要是看得上,那就让给您。尝着好吃,下次姐还给你带!”
这厮果然经不起折腾,怎么说也是厂里的“摩登青年”,一听茅房二字,登时变得嫌弃。我正要把他要的东西塞给他,谁料他却面露难色,推辞道:“不用了,不用了,下次,啊,下次……”
我甩过头,大步流星走进厂房,大可当此事没发生。

04.
其实,我的恋爱之路倒也不是暗无天日,什么年代都有好心人,我也碰巧遇到过一个。
隔街早点铺的乔大爷,是个大善人,在他饱经沧桑的每一丝皱纹里,似乎藏着他对所有生命个体的珍惜和尊重。

有一次,我去他家买油条,他看看周围没人了,问我:“丫头,我有个侄子是个医生,老婆难产不在了,留下一个小小子。你要愿意,我就给你说说。”
我点点头,大概是被上次那两个大婶戏弄出经验,虽然答应下来,但接下来三缄其口,静观其变。

打开我家14寸的大电视,透过崩崩闪跳的雪花,在一部叫作《射雕英雄传》的片子里,依稀可见黄蓉撩开轿帘,喊了一声“靖哥哥”,哇,人世间,竟有如此倾国倾城之女子!
我虽然硬核刚强,但如果白给一个靖哥哥,我也不会狠心说不要。也许我的靖哥哥是个慢性子,在路上耽搁了:希望不灭,日子依旧活色生香。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次分解。
前情回顾1:《归来》上篇|贵为舞蹈皇后的我,为何在毛纺厂终此一生?
前情回顾2:《归来》下篇|日日坚忍,天天救赎,终迎属于我的拨云见日
我是爱电影、爱读书、爱写作的85后写作者,笔名“扬绛心”,喜欢请关注@读书人的成长日记,或者点赞、评论,都很好,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