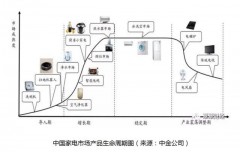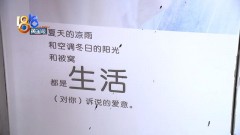文/林丹
泉城的四季,天空灰蒙蒙的时候多些,如患眼病的人,只看得见灰扑扑的一片。蓝天是蓝天,白云是白云,这样轮廓清晰、层次分明的时候难得一见。
冬日的小区,大白天因人们上班的缘故,偶尔传来几声“卖大米”、“磨剪子”的吆喝声以及外面马路上摩托车轰油门、汽车按喇叭的声音,显得越发的空旷、安宁。小区道路两旁的白杨早已谢顶,枯黄的树叶抖落一地,小车偶尔驶过,惊起一群啄食的麻雀,三三两两地落在前面不远处……
我坐在桌前,打开电脑,处理了几封邮件,接了几个电话,起身倒茶,这才发现,飘窗外的泉城,今日竟然格外晴朗。阳光拱出云层,如水倾泻,透过半开的百叶窗,斑驳地洒在身后米黄色的墙壁上,和着屋里的暖气,弥漫出一种暖丝丝的舒适与慵懒来。远处的千佛山青黝秀丽、突兀可见,杯里的金骏眉香气扑鼻,氤氲开来。
“清洗——油烟机——”楼下传来一阵先扬后抑的揽活声。家里刚好有一台欧式油烟机,既难拆装又不好清洁,妻子已唠叨了好几回,我连忙推开窗户,探出半截身子,朝着楼下大喊:“哎,老师,八楼……”
不一会儿,门外响起了重重的敲门声。我刚一开门,一股冷飕飕的穿堂风顿时钻进屋里来,一个老头站在楼道里,面容黝黑,皮肤粗糙,身上裹着一件不大合体的羽绒服,脏兮兮的,绷得上身紧紧的。老头头也没抬,问了句“厨房在哪里”,手里拎着个拧螺丝的起子就直奔厨房,身后的木地板上留下一长串灰白的泥脚印。妻子手里拎着双专门给客人穿的布拖鞋,不满地蹙了蹙眉,我也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
过了半个时辰,老头上楼提了两壶开水,我估摸着老头的活快干完了,就下楼去看。老头正背对着我,撅着个屁股,嘴里哈着热气,埋头清洗着油烟机,一双皲裂的手满是油污,黝黑的脸上渗着细细的汗珠。我不经意地发现,摆满一堆零件的空地旁边散落着一地的新玻璃碴,我家欧式油烟机的两边却光秃秃地开了“天窗”——那块弧形玻璃罩已荡然无存。我不悦地说:“怎么这样不小心?”老头讪讪地解释道:“扛下楼时卸地上……一拆……它自己滑下来摔碎了……”我真的来气了,明摆着是玻璃罩先落地、磕水泥地上摔的嘛!老头有点难为情了,不好意思地用油污污的手挠了挠乱糟糟的头发,向我再三保证说:“明天我一定给你换块新的装上,我先给你留个手机号……”
我看看老头那双皲裂的手,还有他一脸的愧疚,心里有些不落忍,反正清洗费还没给,脑袋一发热,说:“我相信你……明天我等你……”
第二日的白天,老头没来,我想着这油烟机已是好几年前的款式,玻璃罩要配上恐怕得费一番周折……
晚上,老头依然没来,我的心开始忐忑起来,后悔没留下他的手机号码……
第三日,老头还是没来,在厨房里忙着炒菜、被油烟呛得直咳嗽的妻子没好气地敲着锅沿数落我:“真是越活越小了,这么轻信别人的话!”忙了一天工作、头昏脑涨的我,刚走出书房,就被浓重的油烟味呛了一嗓子,不由得在心里恼恨起老头的狡黠来:“老头啊老头!亏了我相信你!”却也只有自认倒霉,一心想着赶紧吃完饭,好到超市买新油烟机去……
“笃、笃……”门外响起重重的敲门声。
“谁啊?”放着好好的门铃不按,还将个门敲得这么重!我的气正不打一处来,猛一下拉开了屋门——楼道里,立着那个老头!黝黑的脸上露着尴尬的笑容,一双皲裂的手托着一块崭新的弧形玻璃罩,紧紧抱在胸前,贴在脏兮兮的羽绒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