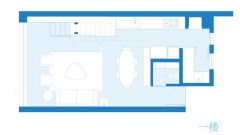罹患精神疾病的人数一直在更新,近十年来增速约18%。
据世卫组织最新估计,全球超3亿人患有抑郁症,但80%的患者却没有接受规范治疗。

图片来自微博@人民日报
这是“情绪病”患者们普遍面对的问题,身边人不理解,自己不承认,不去治疗。
和抑郁症一样,躁郁症也是很难识别,却发病率很高的一种精神疾病。
抑郁症是单向情感障碍,情绪一直低落。躁郁症则是双向情感障碍,有时抑郁难耐,极度无助,有时却异常亢奋狂躁,冰火两重天,情绪像过山车。
“那时我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思考,变得不说话,异常安静。”
前不久,音乐人曹格自曝患上躁郁症,11年婚姻险些破裂。

去年,高晓松的偶像,影响了包括王菲、范晓萱在内的一批音乐人的小红莓乐队主唱桃乐丝·奥瑞沃丹去世时,年仅46岁,已被躁郁症纠缠多年。
而在此之前,梵高、海明威、拜伦、丘吉尔,都曾是躁郁症患者。

爱尔兰国宝级乐队The Cranberries(小红莓)主唱桃乐丝·玛丽·艾琳·奥里奥丹
据权威数据显示,全世界有6000万躁郁症患者,中国就有超700万,且由于躁郁症的识别率和就诊率低,实际上这个数字还应该更高。
也就是说,你身边200个人中,可能就有一个甚至更多躁郁症患者。
几十年前,哈佛医学天才佩里发现自己患上躁郁症时,他并不会知道,未来他将遭遇的一切,有多可怕。
那之后的日子,被记录在这本《自由的囚徒》中,震撼了世人。


“我觉得自己已经被恶魔附身,躁狂感及其强烈。我踱至后院,心血来潮地攀上鹿园四周高达3.6米的铁丝围篱。我撒开双腿狂奔起来。……我想知道自己能否追上鹿群,并捉住其中的一只。”
在佩里20多年的患病史中,这样的躁狂情形,只是常态。

1928年,佩里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几年后更是获得哈佛奖学金资助,专注研究皮肤病,他如愿在医学上平步青云。1931年,他与妻子结婚,事业有成之外,家庭也美满。
苦难是人生的常态,佩里平静的生活,也出现了裂痕。婚后不久,他便躁郁症发作。随即被送进精神心理疾病医院。
他常常情绪亢奋、思维奔逸。为了查看时钟,他爬上家具、跳上钢琴。外出散步,他爬树爬旗杆。力量爆发时,他能举起一张桌子往外扔。
经过近一个月的治疗,佩里暂时康复出院。
佩里并没有痊愈,每当有躁郁倾向时,为了不伤害家人朋友,他躲进酒店,独自一人面对病痛折磨。
除了生理上的折磨,孤独无助以及社会歧视是躁郁症患者所要承受的心理高压。
知乎上曾有躁郁症患者描述过自己被卫生服务站人员冒犯的故事,对方上来就问:“你是xx本人还是xx的家属?你是不是得了精神病?”
像这样的傲慢与粗暴,佩里在韦斯特伯勒州立医院,每天都在经历。

如果没有从韦斯特伯勒州立医院逃走,佩里确信,自己会死于院中。
佩里再次病发,并被抓捕到韦斯特伯勒州立医院,医院护理员把他当作动物般对待。
护理员将在冰水中浸泡过的床单,一层层裹在佩里身上,很快,佩里就如木乃伊般无法动弹,刺骨的寒冷侵袭全身。
随即,被体温捂热的床单,又让佩里的身体如火炉般滚烫。他开始流汗,伴随着盐分流失,小腿的肌肉也开始痉挛。
“即使是正常人,也会觉得极为不适。对此,躁郁症患者——思想与活动都具有持续过度活跃倾向的人——的痛苦程度几倍于常人。”佩里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冰敷治疗结束后,佩里并没有迎来片刻喘息,而是立刻被换上束身衣。这样的来回折磨,需要经历好几个昼夜。
生理上的折磨再痛苦,也远不及心理上的打击来得疼痛。
“你想离婚吗?”妻子的第一句话让佩里措手不及,期盼许久的探望,等来的不是安慰。
“想。”佩里绝望地回答。随即,他们便商定了离婚程序。

富有的,给他更多,没有的,把他仅有的也拿走。入院后的佩里,失去了家庭,失去了朋友,连最后剩下的医生执照,也被吊销。
入院前,佩里预感自己将独自面对一生的悲剧,如今终成现实。佩里常常在想,那些长久住在医院里的病患,是真的病了这么久还是送进来后对世界失去希望才一直生病的。

此刻,在佩里心中只有一件事,从这里逃走。
获得信任的最好方式,就是服从。佩里为了让护理员们放松对他的警惕,对所有的酷刑欣然接受,全然配合。他伺机而动,时刻准备逃跑。
一天夜里,佩里与几个病患在少数护理员的看护下散步。眼前是一片密林,远处的海岸线很近,夜色很浓。护理员背对着他聊天,其余病患各自散步,一切都显得理所当然。
佩里脑子里有一个清晰的声音在说:“跑!”
他钻进密林,飞奔起来,心脏在胸腔内咚咚直跳。不想被抓到的强烈愿望驱使佩里一刻不敢停歇。树枝刮蹭、蚊虫叮咬,佩里仍不敢停下脚步。

佩里如惊弓之鸟般狂奔了好几个小时。
确保已经离医院很远之后,佩里才稍稍放慢速度,直到完全停下来。他仍然警惕的竖着耳朵聆听是否有被追踪的声音,确认没有之后继续赶路。
逃走之后的佩里觉得幸福无比,通过求助远方的好友,他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幸福时光。但命运并没有就此放过佩里,躁郁症常常让他失去心智。
躁郁症的早些年,佩里凭着尚存的正常心智,与病魔及将他看作另类的人抗争。
随后的佩里,在入院与出院中反反复复,并且在家人的同意下接受了当时躁郁症的流行疗法——脑叶白质切除术。
自从那以后,佩里已经不是那个佩里了。他无法独立绑鞋带,无法刷牙,无法系腰带。所有的生活起居都需要人照顾。
佩里生命中燃烧着的火焰已完全熄灭。1954年,与躁郁症抗争20多年后,佩里被发现在浴缸中溺亡。


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数据显示,每年全世界有大约78.6万人自杀。这意味着,世界范围内每分钟都有人尝试自杀。而躁郁症患者的自杀风险是普通人群的10倍。
在与躁郁症斗争的20多年里,佩里接受了冰敷包、拘束衣、胰岛素诱发的昏迷、电休克以及脑叶白质切除术等一系列治疗。
当自杀风险、社会偏见、心理生理折磨统统挡在佩里面前时,他也没有熄灭渴望活下去的生命之光。
后来人们发现,20多年里,佩里一直在研究躁郁症,并期望找到治愈方法。他研究过躁郁症患者的血液与正常人的血液是否不同,还发表了论文《躁郁症的生物化学成分》。
令人惋惜的是,佩里了解躁郁症的速度远没有躁郁症将他吞噬的速度快。在这场与治愈自己的时间赛跑中,佩里彻底输了。
“由于社会的不理解或歧视,产生病耻感选择隐瞒或者逃避有病的事实,在躁郁症群体中广泛存在,而这样会影响病人的疾病诊断、治疗和康复。”原解放军第89医院医学心理科主任图南这样描述躁郁症群体。
在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一念无明》里,余文乐饰演的阿东,在躁郁症好转后重回社会和父亲一起生活,却遭遇了社会冷漠的一面。

被围观,被歧视,甚至被亲近的人埋怨,都让阿东的病情更加严重。


情绪病被污名了太多年,“神经病、变态、疯子……”,社会对其的偏见某种程度上也加重了情绪病的问题。
社会认知不足,导致生病的人不认为需要治疗,治疗的人会遭受偏见。然而他们只是生病了,很多心理疾病是可以康复的,得病的人也不是妖魔鬼怪,他们不应该遭受那样的对待 。

电影中,面对多年邻居的嫌弃,阿东的父亲说:“我不是需要你们帮他,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落井下石。”
一位抑郁症患者说过这样的话:“我做了自己最大的抗争,我在无数次的放弃自己的边缘拯救自己,也许在别人的世界里这些什么也不是,但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我是自己的英雄。”
《一念无明》结尾,这对茫然无助父子,相依而坐。
“情绪病治疗是个长期斗争,治疗创伤的心灵不单需要合适的治疗,社区支援,还需要大众去除负面标签,给予谅解及支持,用同理心去感受和关怀。”
不带有色眼镜、不乱贴标签,了解、包容躁郁症患者,是对他们最大的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