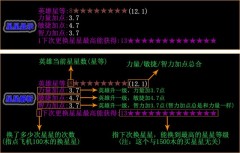“花市,在广州七门,所卖止素馨,无别花,亦犹洛阳但称牡丹曰‘花’也。”这是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屈大均先生在《广东新语》中描写花市的一段文字,寥寥数十个字背后,有着朱悬玉照的百亩花田,有着“富者以斗斛,贫者以升”的清晨花市,有着缠绕在女孩儿发髻上的花梳,有着七夕夜“雕玉镂冰、玲珑四照”的素馨灯,还有着可以消暑清热的素馨球……持续数百年来,这一来自西域的袅娜之花几乎集全城宠爱于一身,拿它与洛阳的牡丹作比,真的不算过分。然而,洛阳的牡丹到今天仍然家喻户晓,我们的素馨却已被淡忘在时间的河流中,“满城如雪,触处皆香”的老广州,也成了泛黄书卷上的故事,渐行渐远。
【花田】
百亩珠悬玉照,家家衣食素馨
翻开记录老广州花卉种植与消费的文献,总能看到一个很诗意的词汇——花田。珠江南岸30多个村庄,人们多以种花为业,花田大者方圆上百亩,珠悬玉照,胜似白雪;城西的芳村有花田,烟水十里,赏花人络绎不绝;西关一带原来是南汉国的御苑所在,花田最盛时绵延九里,直至十三行时期富商纷纷在此修建宅地,规模才渐渐缩减。广州是直到1918年才开始“拆城修路”的,在这之前,这个被周长11公里的围墙“包裹”着的城市,几乎就像游弋于花田之中的一座方舟,花城之称,因此才名副其实。
老广州之所以有这么多花田,是因为人们一直有着旺盛的鲜花消费需求,这与繁荣的商贸传统息息相关。“不当吃不当喝”的鲜花能深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背后断然缺不了钱袋子的支撑。据学者考证,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朝,广州的花卉贸易就有了一定规模,明清时则进入鼎盛期,动辄上百亩的花田,正是花卉商业种植发达的最佳写照。

来自西域的素馨花,袅娜可爱。

居廉水墨本《十香图册》中的素馨花
要说全城花田的主角,则非素馨莫属。这种来自西域、原名“耶悉茗”的小花,千百年来一直是广州人的宠儿。我总是不无偏见地认为,相比较北方人对牡丹的偏爱,广州人宠爱素馨,似乎是更有味道的。《本草纲目》里说,素馨“枝干袅娜,叶似茉莉而小,其花细瘦四瓣”,清代著名文人李渔更因其形态娇弱,一枝一茎都要藤架扶持,直接把它呼作“可怜花”。牡丹的富丽谁都能看见,可素馨的娇弱与袅娜之美,却只有心思更细密温和的人才能欣赏,也只有这样一座气质温润的城市,才养得出这样的人来。
至于素馨花几乎集全城宠爱于一身的盛景,前人留下了大量的竹枝词,如果你有心的话,去翻一翻,就能清晰地感受到了。
【花市】
七城门有花市,一日卖数百担
有花田,自然就有花市。早在400多年前,广州就有了常年开放的花市,且与罗浮药市、东莞香市、廉州珠市并称“广东四市”,其繁华可见一斑。
据《广东新语》记载,广州的花市主要位于七个城门口,即大东门(今中山路和越秀路的交界处)、小北门(今小北一带)、大北门(今大北一带)、西门(今西门口一带)、归德门(今濠畔街一带),大南门(今北京路和大南路交界处)、定海门(今德政路与文明路交界处)。按屈老夫子的说法,这些常年花市上,素馨花是唯一的主角,所以人们口里说的“花”,其实就是素馨,就像洛阳人说起“花”来,其实就指牡丹一样。
虽然全城花田几乎都种素馨,但最出名的还是珠江南岸的庄头村。每天晨曦微露时,村里的女孩子就要起床去摘花了,因为花骨朵一见太阳就会开放,而花一开就不值钱了。
等到天大亮时,一篓篓还带着露水的素馨花就被运到了江畔的花渡头,很多花贩早已驾着小艇在此等候,他们把一个个花篓搬到船上,再驾船穿过珠江,停靠在五仙门码头(今海珠广场一带)。待城门一开,这一篓篓的素馨就会被运往一个个花市,随之再进入千家万户。

庄头花田现已变成了庄头公园。图为海珠区庄头公园。(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苏韵桦 摄)
素馨是最为娇弱的一种花,盛开时也只有细细瘦瘦的四个花瓣,花骨朵更比珍珠大不了太多。所以,广州人买素馨,总要用容器,花贩也都以升计价,一升素馨,要价不过10来个铜钱(1000个铜钱等于1两银子),用屈老夫子的话说,“量花如量珠然”;也有人找来用璎珞把素馨穿成花环,或者找根竹枝,把素馨一朵朵缠上去,一支叫价两个铜板,帮衬者络绎不绝。每天全城花市上卖出的素馨总有几百担之多(一担等于100斤,即50公斤)。
【花梳】
清晓簪上头,月下花才开
真正的大户人家,当然是不用自己派人上花市买素馨的。他们是最受花贩欢迎的长订户。每天城门一开,就有固定的花贩背着满满的花篓,送上门来,这种长期固定的买卖,被老广州称为“担花箩”,而没有“担花箩”的运气,只能走街串巷声声叫卖的小贩,则被称为“提花筐”,正是这些勤快的花贩,将香气送遍全城。
当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花碟,精致的瓷碟里装上清水,放几朵含苞欲放的素馨,摆在案头,又素雅,又好闻,让人时不时想去亲近。人们还会将一颗颗细小如珠的素馨穿起来,做成“花枝”,插入瓶中,很快就有了满屋的清香。
除了装点居室,素馨更大的用处,就是装点女孩儿的发髻了。女孩儿们找来彩丝,小心地穿起素馨,戴上鬓角,这种特别的装饰,叫做“花梳”。清晨刚戴上头的时候,“花梳”上的素馨还都是花骨朵呢,经过整整一天,到了夜晚,它们就全开了,映着院内的月光,或者窗内的烛光,素雅中又带了几分明艳。女孩儿们睡觉时都舍不得把“花梳”摘下来,直到天亮时分,素馨才会凋谢,不过到时又有新的“花梳”可换了。
其实,在更古老的时候,广州人戴花是不分男女的。屈老夫子在《广东新语》里说:“ 南人喜以花为饰,无分男女,有云髻之美者,必有素馨之围,在汉时已有此俗。”两千多年前,陆贾南下劝说南越王归汉时,本地人在发髻间“彩缕穿花”的打扮就让他大大开了一回眼界。

素馨花梳。(来自网络)
素馨不仅可作“花梳”,还可用来美容。巧手的女孩儿将上好的茶油与素馨花仔细拌匀,放入洁净的瓷罐中,用厚厚的油纸封住罐口,再把瓷罐放入盛好了水的大煲中,用小火加热一整夜,就能蒸出上好的素馨油。花油蒸好后,不能马上使用,必须耐心等上10天,才能开罐。素馨油既可用来擦脸,也能用来护发,可以使肌肤莹润,头发亮泽。在那个没有大牌护肤品的年代,素馨油就是最受女孩儿欢迎的美容圣品。
【花夕】
素馨花灯 雕玉镂冰
七月七,广州家家户户都会挂素馨灯。素馨灯做起来可费工夫了,得先找来细细的竹篾,密密地缠上素馨花蕾,再扎成轻巧的灯笼。灯点亮后,蜡烛的热力徐徐发散,催着花儿渐次开放,整个花灯“雕玉镂冰,玲珑四照”,漂亮得不得了。还有很多富家公子哥儿,把素馨灯挂在车头,车过去很远了,空气里还有香气缭绕。
七月七,最热闹的地方在水上。荔枝湾、漱珠涌、沙面、陈塘,数不清的游船在江上徜徉,没有一条船不挂素馨灯的,映着水中的倒影,越发清艳迷人。豪华富丽的紫洞艇上,歌女笑颜如花,客人不醉不归;供平民乘坐的小艇上,一家老小聚在素馨灯下,叫几碗艇仔粥,要两斤河虾,一样自得其乐。江上还有人兜售素馨球,感觉出汗了,拿上一个,揣在怀里,肌肤生凉,有清热避暑的效果。这一夜,满城如雪,触处皆香,七月七,是属于素馨的节日。

清代外销画里卖花的小艇。
素馨在夏天开得最盛,但在冬天也有开花的,人们把冬天的素馨花叫做“雪花”,它们弥补了广州冬天不怎么下雪的遗憾。每到岁尾,广州人总要打“火清蘸”,一个个素馨花环,或摆出游龙、凤凰、流苏等各种好看的造型,以取悦天上的神仙。
祭完了神,当然免不了大摆宴席,如果有人喝多了,主人也会捧出素馨球,喝醉的人闻到寒香,最起码能醒一大半。那时候,整个新年,广州城都会笼罩在素馨的香气中,热热闹闹,又清雅可人。

素馨花不仅清雅也可食用,晒干的素馨花有清热解毒之功效。 ( 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苏俊杰 摄)
曾经集全城宠爱于一身的素馨,又是在什么时候衰落的呢?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洋花卉、新式装饰品和合成香品如潮水般涌入广州,素馨不可避免地失宠了,到了民国时期,它已不再拥有“市花”的荣耀;现在,素馨几乎已经被人们淡忘,而“满城如雪,触处皆香”的老广州,也成了泛黄书卷上的故事,渐行渐远。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王月华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林玮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