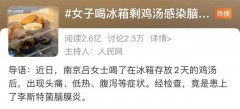作者Lyre
如果没有被按下“受工伤”这个人生的暂停键,按照原本的计划,晓明夫妇现在应在湖北老家开一家沙县小吃,照管着还在读小学三年级的女儿。
2018年,晓明已经开始筹备回家开店的事了。他在一家深圳的工厂为水龙头打磨抛光了五年,但就在离职前五天,协助一个新员工时,他的手套被磨砂齿轮夹住了,连同右手被卷入了高速运转的机器中,一时间血肉模糊,掌关节粉碎性骨折,多处神经拉伤,在医院打了两根钢钉。
等做完康复,晓明发现自己的右手已经握不拢了,被鉴定为八级伤残。切菜时需要用毛巾在菜刀柄包上一圈才能握住,切胡萝卜之类比较硬的蔬菜都有困难。根据《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七~十级属于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五~六级为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一~四级为全部丧失劳动能力)国家人社部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全年认定(视同)工伤113.3万人……超过一半受工伤职工因此丧失部分或全部劳动能力。”
一只左手干不来厨房的活,回老家开沙县小吃的计划也只能搁置,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要上学。一夜之间,四十岁出头还是娃娃脸的晓明愁出了白发。
一篇发表于2018年的论文《生活世界中的疾痛声音》提到,工伤者首先遭遇的是无休止的身体疼痛、身体功能的丧失,接踵而至的则是“人生时序的扰乱”和“自我认同危机”。他们的人生被打断了,家庭的顶梁柱还是顶梁柱吗?还能依靠自己的奋斗改变命运吗?
政府与企业都将工伤赔偿作为工伤事件的终结点,但是“工伤赔偿并不是事故的结束,而是另一个变故的开始,工伤给他们造成的‘人生时序的扰乱’远非一笔赔偿金能解决。”
▌就业:“我还不是废人”
等恢复得差不多了,晓明一边等赔偿一边开始在酒店里传菜,右手端不了盘子,全靠一只左手。一次菜汤洒在客人的裤子上,另一次把红酒泼在别人头发上。虽然客人们都没有为难晓明,但他心里还是会犯嘀咕:“人家结婚,我怕菜摔了不太好。”
第二份工作是在盒马生鲜做拣货员,每天在仓库里忙碌,为外送订单配货。每在配货的塑料袋里装进一种商品,晓明就可以拿到两角钱的报酬。但商品装袋之前要扫描条码,别人一气呵成的动作,晓明只能用不太灵活的左手来扫码,经常要重复好几次才能成功。这份工作做了一个月,数据显示晓明配每个单的时间耗时太久,他被辞退了。
这次找工作失利后,晓明又开始赋闲在家。“老婆天天给我脸色看,我没办法,就去求一个老乡。”老乡介绍他去深圳龙岗新开的楼盘做保安。他成功应聘上了,上晚班,日夜颠倒,算上加班,一个月挣四五千。
稳定工作是有了,但收入比受伤之前每月少了3000多块钱。上完晚班,趁着上午还精神,晓明去做同城闪送,在深圳,3公里以内的单子能拿到14块多。一次晓明从写字楼送东西到某商业中心,3.8公里挣了28块。闪送是按距离计算报酬,时间也不像送外卖那么紧张,晓明经常提前半小时送到,时间充裕,还可以坐公交地铁去目的地。因为受工伤办理了残疾证,搭车不用花车票钱,一单挣得比一般人还多,他甚至跑过100块的单子。
除了打工挣钱,晓明还一直盘算着工伤后拿到的赔偿金要怎么投资,在公益机构的帮助下,他又开始重新考虑开早餐店和沙县小吃的可能性……因为疫情,晓明还在观望,也不敢贸然出手,并在摸索工伤后的生存之道,“如果全部恢复是一百分,我现在大概恢复到六七十分了。今后还是要看我能不能创业,如果弄成了,那证明我还不是个废人。”
以广东省康复中心收治的工伤工友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项调查显示,68.9%的工伤工友成功复工。尽管路途艰辛,但回归人生正轨的过程,让许多工友活出了新的自我。
▌创业:不再回去上班
在东莞东坑镇的一个工业区,每天早上七八点,正是工人上早班、下夜班的时候,王春秀的早餐摊位就会准时出现在人流交错的街道上。她将热气腾腾的几种不同口味的粥装在擦得锃亮的保温桶里,放在木桌上一字排开。儿子负责招呼客人,包装粥和豆浆,用二维码收钱,王春秀则把制作鸡蛋汉堡的炉具架在三轮车上,忙不迭地刷油、煎蛋、倒面糊,做好的鸡蛋汉堡金黄饱满,滚烫地汪着油,整齐地码在一旁。如果不凑近细看,很难发现她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各缺了一截,露出光秃秃的指节。

▲王春秀在早餐摊位用断指比了一个剪刀手。© 作者供图
王春秀刚刚升级了炉具,一炉可以煎18个鸡蛋汉堡,2.5元一个,粥3元一杯,饮品除了豆浆又上新了玉米汁,每天的毛利从最开始的两三百块增加到了五六百块。早餐摊的招牌是皮蛋瘦肉粥,保温桶见了底还陆续有顾客来问。王春秀说,自己选的都是最好的里脊肉,买回来再一刀一刀切碎,手切而不用绞肉机绞碎,就是为了让顾客看见吃进去的都是真肉、好肉,“人家不傻的,他们一般过来买粥,顺便带几个饼。”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里脊肉冰凉,王春秀的断指冷得发麻,儿子心疼妈妈,“让我做不就行了!”
王春秀52岁,已到了领退休金的年龄。儿子30岁,是个出租仓库、门面的二房东,儿媳妇说以后不需要奶奶带孙儿。但王春秀觉得,总要干点事,否则人就废了。
2019年11月,王春秀断掉了指头,她在佛山一家五金厂负责把用冲床加工好的产品从模具里拿出来,一次取产品时机器出了故障,成吨重的冲床突然运转起来,像鸡啄米一样在她的右手上冲压了两分钟,两根指头当时就碎了。
受伤后,厂里一开始不接电话,后来试图只赔两三万就打发她,王春秀寒透了心。在医院气得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她收到了佛山市顺德区乐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下称“乐行”)的普法册子。有了乐行的法律支持,王春秀以涉嫌人身伤害把工厂告上了法庭,最后拿到了七万元赔偿金。但对于法院裁断她个人要承担百分之三十责任,她一直耿耿于怀,“明明百分之百是他们的责任!”
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条,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六级伤残的,可以保留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由用人单位安排适当工作。而九级、十级伤残因为还保留着大部分劳动能力,也可以回到原公司、原企业继续工作,这也是工伤工友回归社会的一个选项。在2017年东莞市同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下称“同耕”)发布的《工伤职工康复再就业需求调查报告》中,29%工友考虑留在原单位,17%工友愿意留在原岗位,但往往要在工伤赔偿上做一些妥协才能继续留在厂里。
这条路对王春秀行不通。她一开始回到了原企业,但被调离去当保安,看大门。不仅工资不如以前,还要每天去打开以她的力气根本推不动的铁门,不时还要做广播体操,忍受种种“特殊对待”。友维工友公益服务中心(下称“友维”)的工作人员也见过类似情形:“还有一种特殊对待是公司社保照买,但不安排岗位,工友觉得这样也不是个办法,还是解除劳动关系算了。”
拿到赔偿离开原企业之后,王春秀又进了一家生产医疗用品的工厂做临时工。手拧不牢螺丝,只能做别人挑剩下的活,王春秀做了二十几天,觉得自己年纪大了,还受过工伤,免不了被歧视。
王春秀后来得知深圳有一家为工伤工友培训做早餐技术的早餐店。通过友维的联络和资助,她在深圳见到了只剩下左手,却把早餐店开得红红火火的陈师傅,并花了10天在砥砺左撇子再就业项目组(下称“砥砺”)学磨豆浆、煮粥、做肠粉。“我佩服他,19岁受工伤,很多人一双手都还不如他。”她现在出摊时,还会把印有“左撇子”三个字的卡其色帽子戴在头上。
社会工作者宋刚虎是同耕的创办人,他认为,从工伤发生,到拿到赔偿、完成身体心理的康复,最后回归社会,一般需要5到8年的时间。王春秀不到一年就完成了整个过程,在维持生计之外,还能追求自我价值,这种案例是不多见的。“这是能力比较强的,能力比较弱的,缺乏家庭、社会支持的,可能人就垮掉了。”
▌投资:P2P骗局与被踩烂的炸鸡店招牌
受到工伤后,经过保险赔付、与厂方谈判协商或劳动仲裁艰难的拉锯战,在报销完医疗费之外,劳动者往往能拿到一笔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赔偿金。这笔钱当然无法完全弥补身心创伤,但如果使用得当,甚至是可以自我发展改善生活的。友维工作人员跟踪的一位七级伤残的工伤工友,四十五岁找不到工作,就用赔偿金加盟了一家奶茶店,撑过疫情生存了下来;砥砺的工作人员小侯跟踪的一位职业病工友以赔偿金作为起始资金,最后开了一家4S店。
宋刚虎回忆起几年前自己帮助过的一个少年, “他去拿工伤赔偿时,眼神飘了起来,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赔偿金如果投资不慎,很快就会赔光,使已丧失一部分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再度陷入困境。
李飞就是这样一位不仅赔光了所有赔偿金还背上不少债务的工伤工友。李飞戴着方框眼镜,腋下夹着笔记本电脑,西裤笔挺,皮鞋一尘不染,每天出入东莞最高档的写字楼和酒店,他现在一边考察比特币,一边琢磨着外汇的涨跌。
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开口闭口“外汇”“比特币”的人,曾在大西北摘过棉花,还在工地上受过重伤。2012年,李飞从售楼处的三楼摔了下来,手脚关节摔断,肋骨断了好几根,肺部破裂,当他躺在重症病房里,“好像天都塌了。”
李飞出院后被评定为七级伤残,工地赔偿了三十二万。当时的他还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笔钱,本打算先为自己买一份保险,发现保险公司还在招人,于是入职了保险公司。
一脚踏入金融圈之后,李飞才觉得自己之前真是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除了干活吃饭吹牛,外界的知识,就是一问三不知!”李飞说的知识,指的就是股票、外汇、比特币那些看起来能钱生钱的知识,他开始觉得打工是没有前途的,学会投资才能咸鱼翻身。李飞从来不去推销保险或理财产品,他到处拜师,参加讲座,考察项目,“学习探讨”。这家公司的试用期过了,没有业绩,李飞就跳槽到另一家风头正劲的公司去学习新的知识,把驻扎在东莞金融地标台商大厦里的公司轮了个遍。
2013年、2014年P2P流行起来,李飞紧跟潮流,入职了一家P2P公司。当时P2P的年化率是12%~16%,远高于银行利率,电视上、大街上到处都是这家P2P公司的广告。李飞在公司亲眼看到东莞的一对夫妇,一口气投了七八百万,他也把这几年攒的八万元,连同三十二万元赔偿金一起投入了公司的P2P项目中。
2015年底,李飞在QQ群听到了公司出事的消息,一夜之间,街上的宣传品全部撤下,这家看起来前途无量的P2P公司被定性为非法集资,相传不仅在离岸开设了银行,还做了假账。他这才反应过来,“这是个骗局!”四十万元也打了水漂。
到了2017年,追讨无望后,李飞研究起了信用卡,一口气套现了12张信用卡。债务逾期未还,到今年十月份,他已经做了一年零八个月的黑户,收到了数不清的律师函,一天要摁掉二十几个追债的电话。李飞还会假装别人接起电话,告诉对方说你们追的这个人不在东莞,到外地抢险救灾去了。
这些套来的现金,都被李飞捏在手里。一来他害怕自己突然生个大病,或出意外;二来他一直在观望别的投资项目,手里有钱,才有翻盘的机会。
投资金融产品充满了风险和陷阱,投资看起来正儿八经的实业也容易失手。小吴二十二岁时被印刷厂的烫金机夺去了半截手臂,被鉴定为五级伤残。五年过去,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打官司,工厂至今也没有付完赔偿金,而人身意外险赔付的钱,全砸在了开XX鸡排店的生意里。
小吴本来只想投资,没想到原本要当店长的合伙人退出了,只得自己硬着头皮去经营。店址一开始选在深圳的坂田地铁口,因为租金太高又开回了老家,炸鸡店迁到了看起来人流鼎盛的广西民族大学附近。但如果不下血本发传单的话,营业额就上不去。“没办法,就是熬,等一个小白摸索出来,已经亏得差不多了。”小吴眼睁睁地看着第一天的营业额上万,然后逐天下降,一直停留在八百元左右,负担人工、房租的成本都很困难。为了把鸡排继续炸下去,小吴花完了积蓄,就找亲戚们借钱,“而且不止借一次,搞得亲戚都以为我进了传销组织。"
2018年夏天,实在干不下去了,小吴把XX鸡排的招牌摘了下来,踩了个稀巴烂。“踩烂了才能退加盟费。”今年,他告保险公司的官司胜诉后,拿到二十六万元的赔付,等还完了欠亲戚们的债,小吴卡里只剩下一万块,干脆跑到贵州,痛痛快快玩了一个月。
▌难题:缺少证书,却有伤残和“案底”
兜兜转转一圈后,小吴到了砥砺,当了全职公益人。今年砥砺发工资有困难,他也没有离开。在一个教工友如何计算工伤赔偿的普法活动上,他作为主持人对所有人说:“你们不要看法律条文这么复杂,我开始也是什么都不懂,但我能学会,你们也能学会”。
这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截过两次肢,告过工厂、保险公司、社保局,能搞懂专业律师都没见过的法律难题。他的微信名是“不动声色的中年男”,来咨询法律问题的工友隔着手机总以为他经验丰富,年纪很大了,他也不说什么,只是嘿嘿一笑,“叫‘大哥’就对了。”
其实在投资XX鸡排之前,小吴也找过工作,跑了广州、东莞、深圳的残疾人招聘会,去应聘过保安、超市理货员,但始终没有公司愿意招他。少掉一只手,受伤前操作烫金机的技能已经没有意义。“愿意招外地残疾人的,会嫌你手残疾了;能接受手部残疾的,又要你是本地人;再加上也没有技能,我辍学,高中都没有读完。”
一些受伤严重、办理了残疾证的工伤工友,可以享受扶持残疾人就业的优惠政策。1990年出台的《残疾人保障法》,规定各地企业应录用残障者的最低比例在职工总数的1.5%到2%之间,即每100个员工中,就要有一到两名残疾人,不达标则应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下称“残保金”),残保金按照差额人数乘以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来计算。企业规模越大,需要缴纳的残保金数额就越高,一些企业为了减免残保金,本应有动力招聘工伤工友,但又很难真正惠及到小吴这样手部残疾的工友。“有意愿、有能力招聘残疾人的企业,多是电子厂这样的企业,对手部的要求相对高一些。”
除了伤残,缺乏技能,工伤工友再就业的另一个难点是,在公司眼里,他们打过劳资官司,熟知劳动法,有了“案底”。“有一些公司也不在乎伤残,只要能做事就行,但特别忌讳工伤,你以后到了我这里,会不会受伤?会不会也找我赔钱?”
薛卫华原在深圳坪山工业区的一家生产汽车部件的大厂里当机修组长,考了钳工证,还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电工,一连好几年都是“优秀员工”。2018年11月,他的左手被工厂的灯管划伤,一片比筷子尖还细的灯管碎片像子弹一样飞进了他的手掌,割断好几根神经,现在他的手掌发麻,一截手指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弯曲,还在手上留下了一道小蛇一样蜿蜒细长的白色伤疤。
薛卫华工伤后请假养病时,在没有结清工资的情况下被工厂违法解雇。厂方咬定他是旷工。薛卫华只得去申请劳动仲裁,厂方称已经在公司公示栏张贴了催促薛卫华上班的通知书,劳动仲裁的裁决是:“……也应通过邮件、微信及电话等形式催促申请人回公司上班,而不是仅在公司内部的公告栏上张贴催促上班通知书,其没有尽到合理通知的义务,应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工伤后薛卫华先去了一家生产钟表配件的工厂面试电工。面试官是一个女经理,要他画电路图,他一只手握笔,另一只手压住纸张,女经理眼尖看到了薛卫华手上的伤疤,马上警觉地说:“你这肯定是工伤,我们不要。”还有一个面试官直接告诉薛卫华,“只要劳动仲裁过的我们都不要,不管你说不说实话,我们都会去调查。”
薛卫华还给同一个工业区的十几家大企业投过简历,全部石沉大海。这让薛卫华推测这些大企业的人力管理、行政之间有一个信息网络,“我估计他们内部有个黑名单机制,把我搞到黑名单里去了。”
这让薛卫华感到无比委屈,“我就不明白了,既然上一家公司违法把我解雇,我申请劳动仲裁难道错了吗?”薛卫华进不了那些工资高、相对正规的大企业,现在找了一家规模较小的玩具厂“混碗饭吃”,“大厂都有法务查你劳动仲裁的‘案底’,小厂都是老板自己在管,没有人手查。”他在这家厂既做电工又做机修,每个月拿六千块钱,比之前低了两千块。他还要照顾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其中,老二是一个智力障碍者,十五岁还像半岁小孩。
▌办法:新岗位、培训和考证
疫情爆发前,老张就在TTI科创集团(下称“TTI”)上班了,他在仓库里负责拆箱。TTI生产和销售电动工具,出口到北美,有超过两万名雇员,站在TTI的入口处往里看,目及之处全是厂区,里面还有小卖部、ATM机、咖啡馆……因为疫情和中美贸易战,公司订单有所减少,老张的加班也变少了,但九月份行情回暖,到处都是招募工人的广告。
老张在以前的公司被砸伤了双脚,现在已完全看不出曾受过伤。TTI招聘老张的时候明确知道他受过工伤,他还看到公司招了只有一只手的残疾人开电梯。此外,如果内部员工介绍一个残疾人进来,工作满半年,介绍人就可以拿到一笔奖励。
友维去年八月曾组织过一些有残疾证的工伤工友去一家大型电子厂的车间,看有否合适岗位,其中两个工友成功入职。当时友维的工作人员为了在东莞找到愿意招聘残疾人的企业,打了无数个电话。“我收集到的四五十家招聘残疾人的企业,其中给工友买社保的只有十来家,待遇与正常人一样的只有七八家,会另外为残障人士设计岗位的只有一家。”

▲会为残障人士设计岗位的TTI一角。© 作者提供
尽管有减免残保金、减税的优惠政策,但真正接受工伤工友、愿意为残障人士设计岗位的企业依然稀少。原因之一是残疾证“挂靠”的现象一直存在。企业帮残障人士缴纳社保,但并不需要他们真的在企业里工作,交社保的钱比交残保金少,相当于为企业节省了成本。
陈小仓是个90后,在五金厂的流水线上失去了三根手指和半个手掌。他现在每天送半天外卖,剩下半天做卖二手电动车的生意,是个自由职业者。一个偶然机会,陈小仓知道东莞某公司可以挂靠社保,于是找了十几个没有正式工作的工伤工友,让那家公司帮他们办理了集体社保,中秋节还会发月饼。“小仓去那个公司,和人力资源谈谈,让他们安排几个残障人士工作,一方面他们工作能力真的没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实现残保金政策的本意。”宋刚虎说道。
除了岗位少,砥砺的工作人员小侯认为,工伤再就业之所以困难,也是因为工友找工作时很盲目。“培训要包括让工人了解自己的能力,学习培养新的能力,社会上对他们投入的资源太少了,导致工人工作了十多年,仍然不知道自己除了普工还能做什么。”她举了一个例子,有位工伤工友听说开货拉拉能月入一万,于是跃跃欲试地想考驾照转行,“别人月入一万,你能月入一万吗?做货车司机,怎么入门?除了考驾照还有别的什么东西要准备?日常可能需要处理哪些问题?出现问题时可以找谁去问?”
为了帮助工伤工友减少这种盲目性,砥砺策划了一个线上的“打工百行”系列活动,邀请各行各业的老师傅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故事,让参与活动的工友对自己感兴趣的行业有个大致概念,再看到底适不适合自己,避免消耗无谓的时间和金钱,做好合理的职业规划。第一场活动邀请了一位面点师傅分享20年的行业经验,和他转行做电工的心得。
友维建议工伤工友,受了工伤后如果还想保持原有收入,可以尝试通过考证来提升技能,去弥补已经丧失掉的那部分劳动能力。友维工作人员咨询过很多提供考证培训服务的学校,也从人才市场了解到,只要有电工证,18~60岁的工人都有企业愿意招。东莞安监局的网站上显示,考电工证是有补贴的。而在不同的地区,缺人的技术岗位各不相同,考焊工证、叉车证都可能得到补贴。
2018年,友维的工作人员介绍一位脚受过伤,十级伤残的工伤工友去学习电工。这位工友在2019年拿到了电工证,后来得到一份主管兼电工的工作,收入比受工伤之前还高出两三千元。建立自信后,他还想跳槽到更好的公司。但也并不是每个工伤工友都有这么好的运气,找友维咨询考证的工友很多,但真正拿到证件且找到好工作的,“十个里面只有一两个吧。”
或许真正最好的办法,是不再有工伤发生。
(文中晓明、小侯、李飞、小吴、老张、陈小仓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