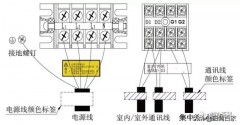我小的时候,气候好像比现在更有个性,起码四季是分明的。过了五一,家里就得换下床单和丝棉被,改铺席子。如今似是而非,春天来得格外晚,似乎它觉得吃亏,临到要走却耍起赖来。
再过些日子就快到黄梅天了。这个时候,菜场上的鲫鱼又多又便宜,尤其是个头不大的那种,简直跟不要钱似的。后来听说这种叫“发水鱼”。不知道是因为天气闷热,鱼在水底不舒服,想要到水面上来透口气,因而更容易落入渔人之手,还是雨多河水涨起来,把鱼冲上岸了?
“发水鱼”
说到鲫鱼,想起最近入手的那本有意思的书,叫《知味难——中国饮食之源》,里面提到,早在先秦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在吃油煎鲫鱼了,《楚辞》中提到过的“煎鲼”即是。这菜夹杂在一推“煎鸿鶬”(油煎大雁)“苦狗”(苦味调制的烧狗肉)“胹鳖”(炖甲鱼 )“臛臇”(红烧大龟)之中,反而因为它的朴实正常(以如今的眼光)而显得格格不入了。

先秦
如此有历史的菜却一点不沧桑,很家长。身在鱼米之乡的我几乎从小吃到大。虽然不至于有段时间不吃就念叨,但如果想起来,脑袋里第一反应出来的就是爷爷做过的那种味道模式,格外亲切。
我在三伯伯(镇上的人对爷爷的称呼)家吃过十多年的饭。眼看着他家从小灶头加煤炉慢慢转变为煤气灶加电饭煲。不过他用来炒菜的好像一直是口纯黑的铁锅,有两个耳朵,没有手柄,很重。外加一把铲子。
就用这俩家伙,他煎的鱼从来都是完完整整的,没见破皮断尾过。
我小时候不爱吃鱼,尤其讨厌红烧鱼块(我们这里叫烩鱼)。但是爷爷的油煎鲫鱼我爱吃。鱼皮煎到将焦未焦,再下酱油、料酒、汤焖透,起锅前撒葱花。鱼皮鱼肉浸透了汤汁,一点儿也不腥。甫一入口,是汤汁的甜咸鲜,经过牙齿和舌头配合小心剔除鱼刺,继而尝到鱼肉带点嚼劲的质地和自身的鲜甜。
我现在搞不明白的一点是,三伯伯做的红烧肉和煎鱼都会留很多汤汁,供我们淘(拌)饭吃,可这样一点也不影响主菜的味道,尤其咸淡依然很平衡。可我这么做的话,汤就算好吃,主菜也会大为逊色。
搞不明白的还有他煎鱼不破的秘诀。爷爷在世时,我尚未痴迷下厨,我只惦记他做的菜好吃,却从没想起要让他教我。如今想来甚是遗憾。
我换过许多锅,看过许多书,煎鱼不破仍然只是偶尔撞上的运气。不过仔细想想也坦然了。爷爷那时候七点半上班,四点半下班,中午也来得及回家做饭吃饭,不知加班为何物,退休以后更不必说,有的是时间笃坦悠悠慢工出细活。
我们么,还是用薪水换时间吧。把钱交给商家,去换一口口“新型涂层”“不含涂层”“纳米材料”……的不粘锅。
今天大先生买了四条号称野生的鲫鱼,个头小,他在处理的时候干脆把鱼头都给去掉了——理由是“没有肉还费调料”,以至于我做出来的这盘油煎鲫鱼没了美感,更没了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