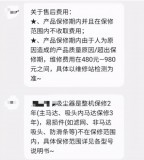说的是厨炊。一个“炊”字,使人想到诗意的乡下炊烟。但事实上,炊烟要在诗歌里才具有诗意价值,于现实中,却是个十分刚性的存在。人类以钻木取火获得熟食,从而把自己跟别的动物区别开来——问题是,锅儿里要有煮的;紧接着锅底下要有柴火把它煮成熟食。而要把食物弄熟,就得支锅打灶,烧柴烧草,以及草原牧民烧牛粪。千百年来,都是如此;世世代代,没有改变。我们插队农村那些年,最沉重同时也最痛苦的,就是上山找柴。早早起身,爬到深山里去,又渴又饿又累一整天,到夕阳西下挑回来一担柴,才几天就烧完了,又得去找。我曾研究过这个“灶”字,从火从土,倒也简单,但这是后来的写法。它的原始写法却复杂多了,竃,从穴从土从黾,意思就是不断的往锅底里塞入干柴,在我眼里就是个深不见底的魔窟。如此这般,直感觉上山找柴,是我辈一眼望不到头的苦刑。幸而我们插队的安宁河谷主产稻谷,一年里有半年烧谷草。但是谷草并不好烧,火一燎过就成黑的,要不断地用火钳去撩拨,弄一顿饭,你得灶前灶后团团转,火钳锅铲同时舞。更要命的是,那谷草你得绾成草把才好烧,那么,每日收工回来,再把晚饭弄出来吃了,再累,沐着月光,或者摸黑,你都得把第二天要烧的一堆谷草把绾好。这甚至成了一天里最后的又不得不服的劳役。后来就返城了。返回城里,烧蜂窝煤。
蜂窝煤按计划供应,每个月,掐着时间,攥着钱和蜂窝煤本子,挑一副自制的担子,到煤厂去排队,在一台黑不溜秋的蜂窝煤机前,眼瞽瞽看着那机器老母鸡般,慢吞吞地,把一个一个的蜂窝煤球“下”出来,下够一家人的再下后一家人的。百无聊赖中,我感觉那刚“下”出来的蜂窝煤球甚至带有老母鸡屁股里的温热……终于把一挑蜂窝煤买回来了,盘进屋里码好,一日两个三个,对付一段日子。烧蜂窝煤是个技术活。先要弄些细碎柴草在蜂窝煤炉子里打底,点燃火,燃烧到一定程度,烧出来一些火炭了,再把一个蜂窝煤球放上去,并拿一把扇子使劲搧,直到把蜂窝煤底部烧红。在这个过程里,小小一只蜂窝煤炉子,即可以十分夸张又放肆地,制造出狼烟翻天笼罩住一整个生活区的宏大效果。这没有办法,家家都烧蜂窝煤,家家都免不了要影响他人,谁都没有怨言——受不了那呛人的烟熏,你可以抱头鼠窜,跑到远处去躲避一下。到炉底上的柴草烧尽,终于把一个蜂窝煤发燃了,那蜂窝煤却一个劲地只管冒烟,冒那种硫磺味极重的硝烟,直感觉它憋了一生一世的冤屈,只等着这机会才要把它释放尽净,你弄一顿饭急着需要的火势,却迟迟上不来,抓耳挠腮中,你急它不急。但是,饭得弄。事实上,你是在一种热吐吐的半生不熟的状态下,极为勉强又凑合地,才把一顿饭做出来的。是的,好歹把一顿饭做出来了,这个时候,不需要火了,那瘟丧蜂窝煤炉,却挣表现般来了劲头,火势大旺。你只能采取各种技术手段“闭火”——关好下面的火门,再拿若干个指头大的由耐火材料做成的小塞子,把一个个红通通的蜂窝煤孔塞住。又不能全部塞完,全塞完了就把火闭死了,留三个两个孔,全由你拿捏。最后坐上一壶水。能温一壶水,我以为是蜂窝煤炉子的唯一优点——到你来弄下一顿饭时,这一壶水差不多快烧开了,拿它煮饭煮菜或接着烧成开水,都很有利。痛恨的是,你要接着弄饭,这炉子上的火已基本过气,要死不活,十分地不给力了。

不妨现编一个顺口溜:发火不易煲火难,小火大火反起燃。烟熏火燎都不算,未几锅儿已烧穿。这最末一句,说的是,蜂窝煤烟气含硫重,腐蚀性强,用不了多久,就把锅底蚀出了砂眼,无论你是锑锅铝壶钢精锅。这直接催生出了补锅业的兴旺发达。补锅不是仅补砂眼,而是将整个锅底换掉。如此一来,各家使用的锅、壶,未几底部似乎都多了一个“垫子”,看上去不伦不类,那便是后来换上去的底子。为弥补蜂窝煤炉之不足,还催生出了煤油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甚至成了家居必备之物,一旦有家人住院,那炉子大抵就会被拎到医院里去,煮蛋熬粥,直弄得住院部充满了煤油烟气味。我辈手动能力强,自造煤油炉子,竟蔚为风气。犹记得那年头,我们砖瓦厂,一段时间里,不少工人——包括我,十分热衷于此道,下了班,就在寝室里出气不匀地忙活。我本人自觉扳金工手艺不错,做一台14管的炉子自用之外,意犹未尽,又做了两台送给亲戚。这个时候,应时应运而生了高压锅。此物虽不过是在锅盖与锅之间加了一个密封圈,将锅盖扣死在锅上后,勿使锅内蒸汽逸出,却可以大大缩减烹煮时间,省煤省时省事。譬如炖牛羊肉、猪蹄膀之类,通常需要两三个小时,高压之下,半小时甚至20分钟左右,就炖好了,故而迅速风靡于世。此锅之弊是存在安全隐患,单听“高压锅”名,即感惊悚;使用时锅内高压蒸汽直把个排汽阀冲得发疟疾般激跳不已,并尖声啸叫,更教人胆颤心惊。坊间尝闻高压锅爆炸事故,报纸、电视,更不时提醒人们注意使用安全,如此种种,都增加了人们心里的不安。终于,电饭煲这煮饭神器,横空出世了!
不夸张地说,此物之出现颇具里程碑性质——放入适量的米和水,插上电源,纤指一按键,但听“嗒”的一声响,即可不再管它,你尽可以去忙别的事情,比如说去煮菜炒菜。如此双管齐下,到你把菜弄好,饭也煮好了。神奇处是,煮好饭它会自动断电。我以为这一点十分地了不起。揭起锅盖,热气腾腾,软硬合适,还不产生锅巴,饭勺一伸,舀入碗里,张嘴就吃,多么惬意。电饭煲的出现,来得比较突然,以至于我们未能意识到,它事实上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电炊时代的到来。蜂窝煤炉在家庭中的地位由此开始式微。高压锅迅速消隐。煤油炉更俨然成了一个笑话。之后,更有了燃气炉、电磁炉、电炒锅、微波炉、电炖锅、光波炉,等等等等。这些可爱的家伙,人性化,智能化,多功能,可调温,能记忆,既聪明,又能干,尤安全,还乖巧。它们变着花样,排着队,深情款款,走进家家户户的厨房,蒸、煮、煎、炸、炖,烧、炒、焖、焙、烘,无所不能,任你驱遣,供你使用。并且全都一键搞掂,绝不拖泥带水。科技进步,来得如此迅疾!你看,短短数十年时间,人类就挥别了千百年来所袭用的土灶传统。我辈于烟熏火燎中挣扎而出,有幸成为这一华丽转变过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作者简介
蔡应律,1946年出生,原凉山州作家协会副主席。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曾在《诗刊》,《星星诗刊》,《小说界》,《四川文学》,《萌芽》。等刊物发表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作品数百万字。小说《回声》、报告文学《命脉》分获第二届、第三届四川省文学奖、小说《家当》、散文随笔录《氤氲》分获第一届、第三届凉山州文学艺术山鹰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