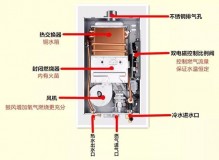【“名家评红楼”系列评论】
宝晴之情的隐性表述
——《芙蓉女儿诔》一处用典的诠释和讨论
作者: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刘上生
宝晴之情是曹雪芹在前八十回精心描写和热烈歌颂的不同于宝黛之恋的两性理想情感。以独立人格为基础的宝晴之情与隐含情欲之私的宝(玉)袭(人)之情的映照,凸显着这种不涉性的异性友爱之情的纯净与高贵。第5回判词与第78回《芙蓉女儿诔》的创造和前后呼应,又使它成为描写最完整的两性情感。

被抹黑的“各不相扰”之情
在第78回宝晴诀别一段里,作者匠心独具地通过滥性女人多姑娘的眼光赞叹宝晴之情“各不相扰”的精神特质,又通过晴雯“痴心妄想,以为横竖在一起”的哭诉揭示这种情感的童真理想内涵。从王善保家的进谗到王夫人视为“狐狸精”的诬指撵逐,暴露了卑俗世态和礼教势力对这种情感的妖魔化,这是导致晴雯悲剧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晴雯去世后的《芙蓉女儿诔》中,作为当事人的贾宝玉为被诬屈死的晴雯和宝晴之情“洗白”不仅出于情感和道义的责任,也必然是驱使其写作诔文的最强烈的内心冲动。
诔文一开始就叙述,晴雯十六岁夭亡,与宝玉相处五年八月有奇,“于衾枕栉沐之间,栖息宴游之夕,亲昵狎亵,相与共处”。十岁起即为侍女玩伴,正是童真少年时代。这明白彰示宝晴之情始自纯净无邪两小无猜的青梅竹马,诔文中提及的“捉迷”“斗草”细节,都是宝玉的难忘童趣回忆。随着年龄的增长,此情始终保持纯真。“其为性也,冰雪不足喻其洁”,没有任何脏污渣滓。这是对晴雯的崇高礼赞,也是开宗明义的洗白之笔。对于“谣诼謑诟”“诐奴”“悍妇”等邪恶势力的摧残,宝玉无比悲愤伤悼。由于文体形式要求和主体意图表达的需要,诔文用了一些典故作为宝晴之情的隐性表述方式,其中包含的历史文化内容涉“性”或疑似涉“性”。不涉性的情感涉性用典,这就造成一些解读障碍。误读则可能失其本旨。全面论述这个问题,非短文所能完成。这里只想举一个流行解读值得商榷的例子,陈述己见,以供讨论。
涉两性之爱解读的质疑
诔文在叙述晴雯悲剧和回忆两人往事后集中抒发内心哀悼之情时,有如下几句:
自为红绡帐里,公子情深;始信黄土陇中,女儿命薄。汝南泪血,斑斑洒向秋风;梓泽余衷,默默诉凭冷月。(据红研所校注本《红楼梦》1982年版,以下引文出处同此)
这是骈体部分的一个抒情高潮。其中“汝南泪血“四句(以下简称“汝南”联)用了疑似涉性的典故。
对此,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红楼梦》的注释是:
“汝南——指南朝宋汝南王,贾宝玉在这里借汝南王同刘碧玉的故事来表达自己同晴雯的亲密感情。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五《碧玉歌》,题注引《乐苑》:‘《碧玉歌》者,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宋汝南王妾也,以宠爱之甚,所以歌之。’”
“梓泽余衷——用的是石崇和绿珠的故事。参见第911页注1。梓泽,石崇的别馆名。”
按第911页的注释“石崇,字季伦,以豪富奢靡著称。见《晋书•石崇传》。”关于石崇与绿珠的故事,第892页注5云:
“绿珠——石崇侍妾名。姓梁,善吹笛。孙秀想要绿珠,石崇不给。孙秀假传皇帝诏令逮捕石崇,绿珠跳楼自杀,石崇也被处死。见《晋书•石崇传》及宋代乐史所撰《绿珠传》。”
启功先生主持的《红楼梦》校注本对此四句注释较详,其基本观点相同,即分别引用汝南王与刘碧玉(并融入唐乔知之与宠婢碧玉故事)、及石崇与绿珠故事;
“这四句都是宝玉自喻(指以汝南王和石崇自喻),表达对晴雯的亲密感情和深切悼念。”(中华书局2010年版,939页)
《红楼梦大辞典》(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的解释与红学所校注本大体相同。不同的是对“汝南泪血”的解释添加了“或谓这里是用汉代张劭与范式的故事”一小段,但并不取此义。也就是说,国内《红楼梦》权威读本和工具书一致认可诔文中“汝南”“梓泽”用典是借汝南王与刘碧玉、石崇与绿珠故事表达贾宝玉对晴雯的感情。
这种解释不无道理。其一,两个典故都包含异性之爱,特别是男性对女子的宠爱;其二,典故中男女身份地位悬殊(刘碧玉、绿珠都是歌女)。虽然这两方面与宝玉晴雯的关系都有相似点,但又显然存在难以使人信服之处。
比拟确切是用典的基本要求。依此解释,却很难感到确切。首先,汝南王与刘碧玉、石崇与绿珠的关系都是主人与侍妾的关系。但晴雯并非贾宝玉的侍妾,连与贾宝玉有“云雨”私情的袭人此时都身份未明,贾宝玉怎么能以汝南王和石崇自比,把晴雯置于侍妾位置,这合适吗?
其次,这两个典故包含的异性之爱,与宝晴之情很不相类。《碧玉歌》最早见于南朝徐陵所辑《玉台新咏》,题晋孙绰作《情人碧玉歌二首》,云“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感郎千金意,惭无倾城色。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感郎不羞难,回身就郎抱。”当是那时情歌。有学者认为或为晋汝南王司马义请孙绰作。至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45,引《乐苑》谓南朝汝南王为妾刘碧玉作,题无名氏五首,有异文。据考证,刘碧玉原为邯郸倡女(据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乐府古辞《鸡鸣》诗注)。梁元帝《采莲赋》中有“碧玉小家女,来嫁汝南王。”应是传说。刘碧玉不知所终,所谓“汝南泪血”自然是没有的事。绿珠确是为石崇殉身了,《晋书》所述耐人寻味:
“(孙秀)遂矫诏收崇及潘岳、欧阳建等。崇正宴于楼上,介士到门。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于楼下而死。崇曰:‘吾不过流徙交广耳。’及车载诣东市,崇乃叹曰:‘奴辈利吾家财。’……”
绿珠之死有其反抗强暴的一面,也表现了对主人的忠诚,但又有可悲的一面。她是一个弱女子,命运完全由争夺的男人摆布控制。石崇的话意思很明白,所谓绿珠殉情实际上是为石崇所逼。这位生活极度奢靡、视女性为占有物的豪富公子对爱妾惨死毫无伤心,他考虑的乃是自己的命运和钱财。难怪人格意识极强的林黛玉在《五美吟•绿珠》(第64回)对石崇之情作了如此的颠覆性评论:
“瓦砾明珠一例抛,何曾石尉重娇娆。”
宝黛心心相印。宝玉明知林黛玉对石崇的批评否定,怎么会在诔文中以石崇自比,视晴雯为绿珠,写宝晴之情呢?
从本质上看,所谓汝南王与刘碧玉、石崇与绿珠的两性之爱,都是权势强大的男性对地位卑弱的美艳女性的占有甚至独占关系。故事中渲染的女性为男性献身,正是男权文化的体现。这与虽身为贵族却以“女清男浊”论反叛传统,视女奴晴雯为清净女儿“第一等”人物的贾宝玉,同“心比天高,身为下贱”最无奴性的晴雯之间的纯情关系乃天壤之别,怎能比拟并提?
生死至情的隐性表述
那么,能不能为这两个典故找到更符合宝晴关系性质的解释呢?
事实上,《红楼梦大辞典》关于“汝南泪血”一条的解释,“或曰这里是用汉代张劭与范式的故事”已为我们提供了线索。它也许反映出编写者当时面对的不同意见,虽然最后没有采纳,但注释的包容态度却能给后人重要启示。
范张故事见于《后汉书•独行列传》,是一个富有某种传奇色彩且极为动人的生死之交的友情故事。山阳(今山东济宁市金乡县)范式(字巨卿)与汝南(今河南汝南县)张劭(字元伯)是太学学友。后张劭不满朝政归家,范式出仕。张劭病重,范式梦见张劭来向他告别,立即告假千里奔赴汝南:
“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驰往赴之。式未及到,而丧已发引。祭至圹将窆,而柩不肯进。其母抚之曰:‘元伯,岂有望邪?’遂停柩移时。乃见有素车白马,号哭而来。其母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丧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异,永从此辞。’会葬者千人,咸为挥涕。式乃执绋而引柩,于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为修坟树,然后乃去。”
这才是真正的“汝南泪血”。元人宫天挺有《死生交范张鸡黍》杂剧,第二折范式梦张劭诀别就有“一梦绝,觉来时泪流血。寸心酸,五情裂”之句,或正为“汝南泪血”所本。张劭把范式视为“死友”,后人称颂范张“生死之交”,因为这是友情的最高境界。这种超越现实功利追求和时空限制的死生至情绝非《碧玉歌》主人写侍妾献身所能比拟,而这正是宝晴之情的根本特色。晴雯无奴性媚骨,宝玉尊重晴雯的人格和任性,晴雯挣扎病体为宝玉补裘,却绝不容许宝玉轻薄。两人内心都深藏着一份挚爱,却始终保持关系的纯真无暇,“各不相扰”。晴雯临终前和宝玉交换贴身小袄以为怀念,宝玉以血泪真情写成《芙蓉诔》祭奠晴雯。“汝南泪血”之典以范张比拟宝晴,把宝晴之情升华为生死之交这一古代友情的最高境界,应该说,这才是贾宝玉的真意,也是曹雪芹的良苦用心。
理解了这一点,对“梓泽余衷”的含义也就可能有新的认识。《晋书•石崇传》:“崇颖悟有才气”,为官就任徐州,“崇有别馆在河阳之金谷,一名梓泽。送者倾都,帐饮于此焉。”石崇与潘岳、陆机陆云兄弟等著名文人交游,有“二十四友”之称。金谷园(梓泽)是其交游饮宴之地。唐韦应物《金谷园歌》云:“石氏灭,金谷园中水流绝。……嗣世衰微谁肯忧,二十四友日日空追游。”潘岳与石崇关系尤为密切,他在《金谷集作诗》写道:
“王生和鼎实,石子镇海沂。亲友各言迈,中心怅有违。何以叙离思?携手游郊畿。朝发晋京阳,夕次金谷湄,……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
后来潘岳与石崇同因牵涉政治斗争就刑东市,有人因此把“白首同所归”视为诗谶。尽管二人的政治操守可议,但潘岳诗中表露的友谊真情还是难以否定的。潘岳另有《悼亡诗》三首,写夫妻之情真挚动人,说明他确是重情之人。“白首同所归”,也算是一种“生死之交”的友情期许吧。
有关史料没有记载绿珠是否在金谷园(梓泽)坠楼。杜牧《金谷园》诗把二者联系起来。但在古籍检索中,没有发现用梓泽代称“金谷”咏绿珠或石崇绿珠故事的例子,而自王勃《滕王阁序》以后,“梓泽”与“兰亭”一起常被文人用来抒发友情和人生感慨。如:“胜地不常,盛宴难再。兰亭已矣,梓泽丘墟。”(王勃《滕王阁序》)“王羲之之兰亭五百余年,直至今人之赏;石季伦之梓泽二十四友,始得吾徒之游。”(王勃《游冀州韩家园序》《全唐文》卷180)“角巾私第,杖策丘园。或追梓泽之游,时习兰亭之赏。”(佚名《唐豫州都督于德荣碑》《唐文拾遗》卷62)等。
如果我们承认诔文“汝南泪血”隐含生死之交的意义,那么,联系有关“金谷”(“梓泽”)的语义和语用追溯,也就不难得出结论,所谓“梓泽余衷”也是借潘岳《金谷集作诗》“白首同所归”诗意表达同样的情怀。而其目的,都是比拟宝晴之情的生死至情并抒发对晴雯之死的极度悲恸。
如此看来,对“汝南”一联典故的意义和功能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以男主与宠妾之情关系比拟宝晴之情,一种是以生死友情比拟宝晴之情。应该说,二者都有语义依据,但在语用上指向完全不同。如果说,前者反映了贵族公子贾宝玉对所钟爱女奴晴雯的潜意识欲望,在诔文中有所表露(这也是笔者以前的认识);那么,后者则反映了贾宝玉面对谣诼诽谤邪恶压迫致晴雯惨死悲剧,勇敢维护生死至情和自证清白的坚决态度。两种解释都可通。前一种解释现在被普遍接受,后一种解释尚未见有人阐述,笔者在反复思考之后,认为后者更符合作者本意,更能成为宝晴之情的隐性表述。倘若硬把“各不相扰”的至情至爱作涉性解读,岂不正好掉进了诬陷者所挖的坑里?
两类意符
用典辨析,不能就事论事,须放在语境中理解。这里笔者想提出两点意见:
一是林黛玉对诔文的修改意见。“汝南”联的前文原是“自为红绡帐里,公子情深;始信黄土陇中,女儿命薄”,黛玉明确批评“只是‘红绡帐里’,未免熟滥些”,提议用现成景事。宝玉改为“茜纱窗下”,黛玉才满意。黛玉不满意的“熟滥”,其实就是“红绡帐里”流露的庸俗的涉性之笔,也正是曹雪芹在第1回批评的“风月笔墨”。黛玉没有批评宝玉用典,说明她理解了“汝南”二典写真挚友情的含义。改为“茜纱窗下”才情境相合,与此一致。可是后人皆据脂批,只注意修改后“我本无缘”“卿何薄命”的“诔晴雯即以诔黛玉”的谶语意义,放过了对涉性“熟滥”的批评。实际上,前者非黛玉所能自觉,后者却是“质本洁来还洁去”的黛玉的本能反应,在对人格自尊自洁的维护上,“晴为黛影”,完全一致。
二是与《芙蓉诔》的宝晴关系用典的整体设置的联系。总观诔文宝晴关系用典,可以看出两种指向。一种以两性之爱的终极形态喻理想追求,这是对楚辞“求女”比兴手法的借用;一类以生死友情故事隐喻宝晴关系的现实形态,表现与传统友情文化的融合衔接。由此形成两类意符系统。前者例子很多,如“镜分鸾别”“共穴之盟”等等,语义显豁,为人所熟知;后者数量较少,语义较深隐,不易察知,却不容否定。其意义首见于诔文中伤悼晴雯夭逝段落的“露阶晚砌,穿帘不度寒砧;雨荔秋垣,隔院希闻怨笛”一联,前句或用沈佺期《独不见》“九月寒砧”诗意,后一句“闻笛”则可肯定是用向秀作《思旧赋》伤悼怀念亡友嵇康吕安的故事:
“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始作赋云……”
“雨荔秋垣”则用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诗“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此诗也是写友情的。此联看似夫妻与朋友对举,用典辞意却明显偏向后者。以曹雪芹崇尚的魏晋“竹林七贤”故事为叙述起点,含义深永。“汝南”“梓泽”二典,正与此意一脉相承,加上后文林黛玉对“红绡帐里”“熟滥”的批评和宝玉的改正,显示出以生死挚友之情伤悼晴雯的另一意符系统。只是由于前一类意符较突出,而“汝南”二典又可作性爱故事理解,故由此及彼,很容易作出涉性诠释,融入前一类。而本来是伤悼友情的“闻笛”一典,又被忽略,在这种解读下,曹雪芹笔下的两类虽有联系但又各有明确内涵的意符变成为内涵混杂模糊的一类,不但使得对宝晴关系的诔文解读与作品对宝晴关系的实际描写完全背离,扞格不通,也严重影响了对独具匠心的《芙蓉诔》的接受和领会。
曹雪芹是伟大的。以塑造晴雯而论,他不但用颠覆传统语义的“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创新词语作为晴雯人格的标志性符号,塑造了文学史上光彩照人的反奴人格女奴形象,还通过对宝晴之情的描写及其诔文的隐性表述,贡献了一种可与宝黛之爱相媲美的两性关系的崇高理想。这种超越于“性”的生物性和社会奴役性的美好情感,在礼教森严的封建社会固然是空谷足音,万目睚眦;但到现代社会已日渐成为多有佳话的人类文明高级形态。正确解读《芙蓉诔》作为宝晴之情隐性表达形式的相关典故,也许不无现实意义吧。(刘上生)
来源: 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